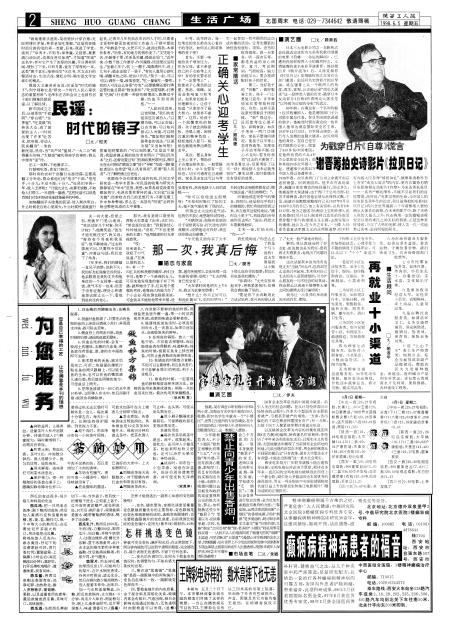
本版导读
民谣:时代的镜子
文/村夫
“做扇婆婆手遮阴,染坊里伙计穿白裙;瓦匠师傅住茅屋,种菜老倌吃菜根。”这是我孩提时祖母教我唱的第一首歌。后来,我进了学堂,读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才知道“民谣”这名字,并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平日偶有所闻,便抄了下来,日积月累,竟有了厚厚的一本。这类“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俚语村言,生动活泼,褒贬分明,确实是文学宝库中的精品。
俄国大文豪普希金说,民谣是“时代的镜子”;列宁则称它是“研究一个时代人民心里状态的重要材料”;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也曾号召干部们搜集民歌民谣,以了解民情。
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前那些“手遮阴”、“穿白裙”、“住茅屋”、“吃菜根”的劳苦大众,成了国家的主人,一时间出现了许多“吐苦水、挖穷根、劳动人民庆翻身”一类的新民谣。然而,当“共产风”猛刮,“一大二公”喊得震天价响,“大锅饭”被吹得神乎其神时,群众中便有“谣”传:
出工一窝蜂,下地磨洋工。
打鼓喊吃饭,食堂门挤烂。
那时有的农村干部整日东游西荡,还要高额工分补助,群众称他们为“甩手”干部:“甩甩手,十分九;不动不捺,十分八。”社员们辛苦一年,收入怎样呢?“日值九分九,决算无钱数。不如给人打帮工,一日混得一餐酒。”这些民谣可以说是百姓们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最早的呼唤。
细细翻阅手头收集的民谣,使人渐次明白:什么时候老百姓心里窝火,什么时候民谣就盛行起来。记得早几年机构改革启用人才时,只看重文凭和年龄而忽视实际工作能力,干群中便流传:“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就讲这两条,本事作参考。”后来,有的地方的情形变了:“文凭是个名,年龄等于零,关系是关键,提拔走后门。”近年来,少数干部工作漂浮,作风腐败,民谣便应运而生:“坐着小车子,转上一圈子,端着酒杯子,说上几句子,临走还提了一袋子。”有的人滥用公款吃喝,酒酣耳热之际,便信口开河:“筷子一起,可以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吃一餐就吃一餐吧,有的人可没这么容易“打发”,还要跳舞还要打牌还要钓鱼且都有“附加条件”:“吃饭要唱歌,打牌要‘巴锅’(扑克牌一种新的赌博法),跳舞动手摸,钓鱼不到用网拖。”……
“人欲自见其形,以资明镜。”我们的老祖宗还告诫后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假如我们按照普希金的说法,“以谣为镜”又当如何呢?答案是明摆着的:“可以知民意。”正是这个原因,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在明白了“国以民为本”之后,还曾设置过专门机构收集民歌民谣。柳宗元在永州得知“赋敛之毒”甚于“异蛇”写成一篇《捕蛇者说》,也希望“观人风者得焉”。所谓“观人风者”,乃了解民情之官吏也。
我国而今没有收集民谣的机构。民间文学研究会一类学术团体,对民谣的收集与研究大都停留在“学术”范围。我想,如果各级党政要员都如列宁、毛泽东那样看待民谣,又自觉“以谣为镜”,经常检点自己的思想行为,不断克服工作中种种弊端,那么这一高悬的“明镜”必将折射出弊绝风清的太平景象。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