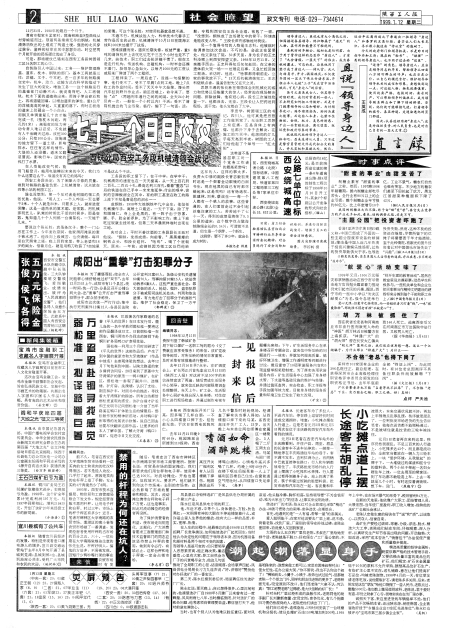
本版导读
七十一日日夜夜
——西铁分局西安工务段机械清筛会战记
12月31日,1998年的最后一个日子。
渭南市程家乡孟家村,陇海铁路呈S型曲线从村旁蜿延而过。顺着两条绵绵无尽的钢轨,机械清筛后吹出的土堆成了两道土埂,强劲的北风穿过狭谷,崖畔的枯草在风中瑟瑟抖动,时空把两个月前开始的那场硬仗抛在了身后。
可是,那场硬仗已铭刻在西安工务段树园领工区54名职工的心中。
自铁路引入中国以来,工务——维护管理路基、道床、枕木、钢轨的部门,基本工具就是三样:洋镐、叉子、牛耳耙。在一百多年的铁路演变史中,机车、动力、运输方式在科学的推动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唯独工务——这个铁路运行的基础部门动静不大,就说清筛吧,人工将钢轨、枕木下面的道碴掏出来,用筛子箩出碎石和土,再将道碴回填,以增加道床的弹性。重4公斤的洋镐高高的举起,又重重的落下,有时在板结的道床上仅砸出一个小白点,用钢叉单调重复几十次才能完成一孔(指枕木间距,两孔约1米),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令常人难以忍受。不免就有人干活瞒天过海,该挖300公分,只挖100公分,该掏通的地方留下一道土埂,影响排水,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大修的人还没撤,道床又翻浆冒泥,影响行车,国家的钱打了水漂。
在人类能改变气候,能用飞船登月,能用电脑模拟未来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干,难道没有其它的路吗?
西安工务段决定:为了保障大中修的质量,做到对铁路的基础负责,上机械清筛,试点放在四等小站的树园工区。
谁也没想到,第一个反对者是树园的领工员张长胜,他说:“用人工,一个人咋说一天也要干2米,十个人就是20米,只要多上人,就有进度保障,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是常数。用机械那玩艺儿,趴窝的时候比干活的时候多,那是变数,鬼知道几十个人伺侯一台清筛机,一天能干几米。”
要说这个张长胜,真是条汉子,整个一门心思在工作上,今年麦收期间,他家渭河滩里的麦子被水泡了,他没向上级喊苦,也没请假,每日里白天照常上班,晚上回到家里,带上老婆和16岁的闺女,借着月色,硬是用剪刀收获了7亩地里的麦穗。可这个张长胜,对使用机器就是想不通。
不通不行,机械战胜人力,科学技术代替手工劳作是历史的必然,机械清筛于10月15日在陇海正线K1006米处摆开了战场。
困难接踵而来,道床长期失修,板结严重,重6吨的清筛机开上去吭吃吭吃干三五个小时也走不了几米。缺技术,职工们过去抡洋镐干惯了,现在又是走行机构、传送机构、出碴机构,一时半会还摸不着门。段领导心急如火,以每月1000元的工资从咸阳某厂聘请了两个工程师。
工程师来了,一周后走了,没提一句报酬的事。他们受不了。受不了早晨7点到工地,晚上7点收工的作息时间;受不了天天中午大烩菜、馒头用汽车拉到野外作业点,碗还没端上,命令来了。要抢“点”(两趟列车通行之间的间隔,全天24小时仅有一次,一般在一个小时以内)干活;受不了清筛机抛出的飞尘污染。临行,搁下了一句话,活,不是这么个干法。
工务段的职工留下了,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机械清筛的速度也在一天天提高,从一天上百孔到二百孔、二百五十孔,最高达到三百孔,看着“整容”以后的铁道在自己手中一米米地延伸,付出的艰辛、尝到的苦辣酸甜全在其中,有的职工甚至在收工的路上流下不知是喜是悲的泪水…
成钢铁,1958年大炼钢铁年代中出生,他担任机械操作手,离喷土口最近,一天干下来,除了牙和眼睛仁,身上全是黑的。有一阵子由于劳累,脚、手、脸全部浮肿。为了不影响工作,晚上下班吃过饭就去挂吊瓶,但第二天早晨照样准时出现在工地。
庆功会上,平时不善饮酒的工务段段长王珏对他说:“钢铁,发扬成绩,向前看。”黑黑瘦瘦的钢铁点头,和段长碰杯,“咕咚”,喝了个底朝天。原来,一年前,成钢铁因为领工区处罚他缺勤,专程到西安找王段长论理,被剋了一顿。“没想到,钢铁成了这场硬仗中的骨干,环境真是能改变人呀。”王段长深有感触地对我说。
另一个值得书写的人物是王忠科,他被临时抽调参加这次会战,不巧的是,会战正在紧要处,他父亲住了院,50多天里,身为长子的王忠科没顾上到西安探望父亲。1998年12月11日,父亲撒手西去,王忠科得知后匆匆赶回,在父亲的遗体前大哭一场……处理完后事,又急忙赶回施工现场。采访时,他说:“啥事都得朝前走,公家的事我放不下。”13天后机械清筛完工,王忠科烧纸点香,遥遥告慰先父在天之灵。
思想不通的张长胜在领悟体会到机械化的威力和优势以后能量大的惊人,经常泡在现场解决问题、排除故障。他有冠心病,段长三次催他检查一下,他都没去。无奈,王段长让人把药送到现场。活干完,他头发都白了大半。
李彦学,树园领工区的书记,四川人。他可真是把思想工作做到家了,无论职工思想上有疙瘩,还是身体上有病痛,他都扑下身子去解决,在施工的71天中,他房间的灯几乎每天亮到半夜,树园的工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红太阳”。
这难道不是基层职工对一个党务工作者的最高奖赏吗?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太多,负责大中修的副段长晋志毅初来时还是一个架着金边眼镜的白面书生,现在他黑的自己有时都怀疑起来,这是我吗?还有杨选权、姚建林、刘英、蔡战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这些普通的、在人们面前走过不会引起丝毫注意的工人,苦苦地干了七十一天,得到的成绩是清筛了9.5公里的道床,这个数字仅占陇海铁路线全长的0.54%,可谓微不足道。但它是一个萌芽、一个新生。
这萌芽,要不了多少年,就会长成大树的。
本报记者韩庚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