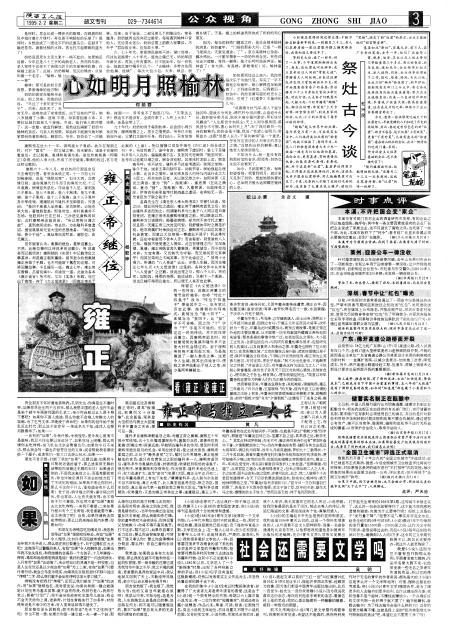
本版导读
雍正帝继位
杨乾坤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曾两废太子胤礽,故尔在驾崩之时,对于“国本”——即立储之事,尚未解决,诸皇子在窥伺着皇位,尤以胤禛、胤禩和胤禵为甚,皇位终被胤禛(即雍正)夺得。他的入承大统,形成了历史疑案。事情的经过,官方是这样记载的:
康熙六十一年八月,帝自热河行围返京后又去南苑行围,看来身体很正常,十一月初七日回畅春园,说是“偶冒风寒”,似非大病,且病情日轻。遂命胤禛代行冬至日的南郊大祀。十三日凌晨,病情忽然恶化,传诸皇子人见。寅刻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皇十二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及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传遗诏:“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其时胤禛并不在场,他赶到时已在巳刻,三次进见康熙帝问安,此时康熙帝还能说话,“告以病势日增之故”。直到夜间戍刻,帝去世,方由隆科多宣遗诏,据说胤禛尚无登大宝的思想准备,“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胤祉等向其叩首,遂即位,改元雍正。
但怀疑者认为,胤禛的继位,是矫诏篡立,不然,此继位事何以传说多而记载少,传说离奇而记载恬淡?康熙朝的《实录》中记载传位之事甚详,却是雍正朝所纂修;留传至今的档案被雍正帝做了手脚,也不可能留下篡位的证据。对矫诏篡位事,今且援引一证:雍正七年,雍正帝在曾静、吕留良案中,有谕旨一道,此谕为各本《雍正谕旨》所不收,又非《实录》所载,但它出于御笔,存于《大义觉迷录》(即雍正帝关于此案的《上谕》,附以曾静口供及忏悔作《归仁录》而合成之书)中,当信其真了。谕中有言,康熙帝下遗诏时,皇七子及隆科多等八人在场,偏偏胤禛不在,及至其代祀南郊“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痛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丑诋之满语,意为“狗”,指胤禩)、塞思黑(丑诋之满语,意为“猪”,指胤禟)等,久蓄邪谋,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伏首臣伏于朕之前乎?”
孟森先生在《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中曾引此谕,驳之曰:据此则传位之遗诏,雍正帝于康熙帝逝世之后,始由隆科多述而知之,而谓隆科多与七皇子八人同以是日寅刻受诏,在雍正帝未至康熙帝寝宫之前。何以既至以后,康熙帝方口语便利,能屡述病情,却为何不言付托之意?况且那一天雍正帝三次进见问安,则舒缓如平时之微恙护视,绝非将属纩时举抉迫切之态,康熙帝可以自达其意之机会甚宽,而竟以大位相授一事遗忘不语乎?到这等时候,还在守秘密而不告本人乎?若言秘密,则受谕的八人已知,唯独不使受遗之人得知,此岂在情理之内?又况胤禩、胤禟,雍正帝既言其久蓄雅谋,希冀储位,而今忽闻末命,大宝有属,又岂能代为守秘,而兄弟间若无其事乎?而其兄弟间之不闻其事,亦于此谕证之。”驳得十分得力。所谓的“八人受谕”云云,亦使人生疑。因为在雍正七年九月《大义觉迷录》出笼前,各种文件中从未有“八人受谕”之记载,该说出笼之日,那八个人中,死的死,囚的囚,得罪的得罪,能说话的,只剩下一个胤祐,但也已被吓得苟且偷生。所以便无人来否定此事。
保留在《大义觉迷录》中的一些传言,说雍正帝篡立的情节曲折离奇,如将“传位十四皇子”改为“传位于四皇子”便是其中之一。但专家已否定此事,按清朝的书写格式,胤禵当为“皇十四子”,胤禛当为“皇四子,此“皇”字不可省略。因之改“十”字为“于”字是不可能的。但否定这一民间传说,并不排斥矫诏篡立,因康熙帝逝世时,控制着局势的胤禛和隆科多不会使大好机会错过的。至于康熙帝病势不重而忽大变,乃是胤禛进了一碗人参汤之事,这更令人生疑。因其出自谕旨中,便较之斧声烛影出于他人之笔,至少是同等嫌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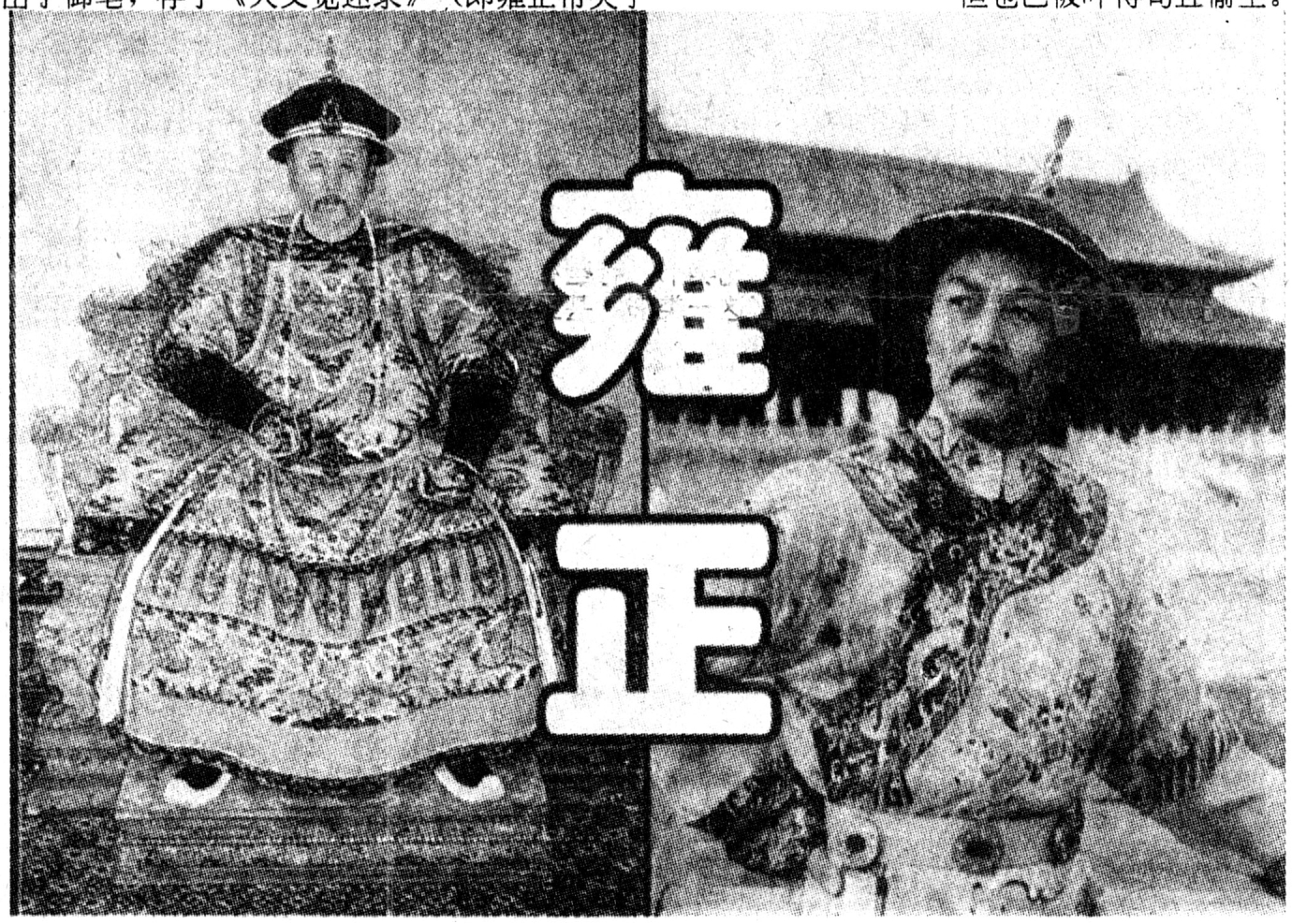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