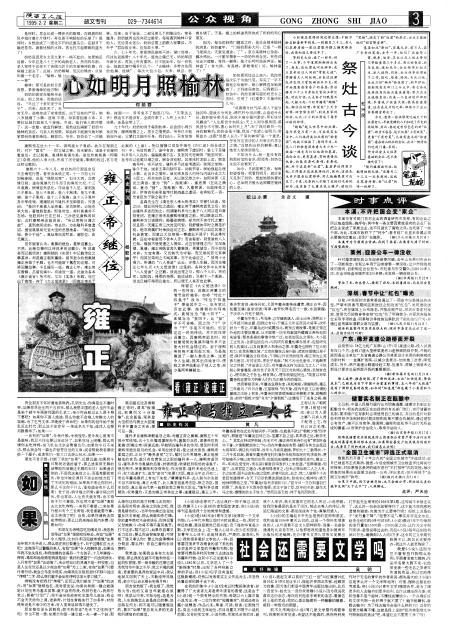
本版导读
社会还需要文学吗
吴明
《小说》杂志停刊了,这让我好一阵子难过。说实话,我算不上《小说》的作者和固定读者,但《小说》的停刊还是使我十分地惋惜和遗憾。
《小说》是1985年由《青年文学》发展的一个文学刊物,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时不时地看过一些,那时文学还热着。虽说经商热已经兴起,但下海的毕竟是少数,文学在社会上、在一般人心目中,至少在校园里、在青年人心目中,还是神圣的、严肃的、崇高的。所以,我和很多爱好文学的人一样,经常要花很多节衣缩食的省下来的钱去买各种文学类的书籍和刊物,经常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读这些书籍和刊物,这其中不必说就有《小说》。1985年以后,文学进入了一个“新探索”时期,出现了各种标新立异的手法,但《小说》似乎没有追赶这股新潮流,仍然以发表现实主义作品为主,并坚持沿着这样的路子走下来。
在我的印象中,《小说》没有以时髦招徕读者,却赢得了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喜爱。这是由于《小说》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刊物:每期以六七篇中篇小说为主,有一二位作家的“短篇集束”,间或还有长篇小说精选,作品扎实、厚重、可读、耐读,它围绕刊名,突出小说的主体地位,栏目设置又不限于小说的范围,又有纪实文学、小说书简、作家风采等栏目,就我个人来讲,我尤其喜欢它的名人传记、小说序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田汉、郁达夫等人的传记,和追忆路遥的文章,都活泼泼有个性,真挚而感人。
《小说》的主编赵日升先生是我的老师和朋友。我和他是1996年夏天认识的。这是一个很朴实很善良的人,从外表看不出文人那种骄矜,很像一名普普通通的北京老市民。从他那里我知道他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老编辑,先办《青年文学》,后来又发展出《小说》,提起文革以前的“三红一创”(《红旗谱》《红岩》《红日》和《创业史》),提起许多西北作家,他都很为自豪,因为他们都是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的。此后一直至今,赵先生一直给我寄赠《小说》,因为我说我喜欢这份杂志。每次收到他亲手寄来的杂志,看着信封上他的笔迹,我的心里总能感到一种融融的暖意,感到一种殷切的期望。
前不久传闻说《小说》等几家文学期刊将要停刊,我感到非常忧虑,希望这不是真的。然而待到我打开赵先生寄来的1998年第6期,这传闻不幸被证实了。这么好一份杂志却要停刊了,这不能不使我感到遗憾和疑惑,究竟为什么要停刊呢?报纸上说是由于“发行量下降”、“经费不足”,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赵先生他们的《终刊词》讲,《小说》最近5年平均每期的发行量在15000册——20000册之间,这作为文学期刊来讲,是很说得过去的。而且《小说》每年还创收利润10万元,编辑部5人人均2万多,这令其它文学期刊称羡不已。既如此还要停办,我这外人就更糊涂了。
我爱《小说》,还因为它不像有些刊物那么势利,尽围着名家大腕转,作品非名家大腕不发,它经常发表一些无名之辈青年作者的作品。所以它的停刊对于无名的青年的作者来说,损失是大的。《小说》这是多么好一个文学阵地呀!可惜。据称出版社的考虑是,将《小说》与《青年文学》精简合并,是为了调更多的人去编书创更多的利。也许这理由很合理,我却觉着不是个滋味。不赚钱或赚钱少,一个办得好好的文学刊物一块好牌子就不要了?编书能赚钱,就都去编书?为了钱去编书会是什么样的书?这样的经营方略真不懂。这就是报上说的“经济转型期文学刊物面临的挑战”吧。难道社会不需要文学了吗?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