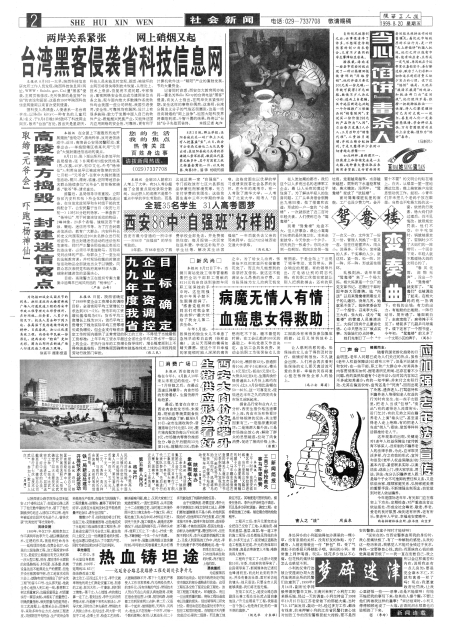
本版导读
鸳鸯楼变奏曲
在人流如潮的都市,我们这个以人多而出名的老牌军工企业,最让人头疼的莫过于住房了。为了解决年轻人的住房问题,工厂从单身宿舍倒腾出九栋旧楼,做了搭建和改造,形成的一户一室的“小鸽楼”,一次就吞进了近二百对年轻夫妻。人们便称它为“鸳鸯楼”。
别看“鸳鸯楼”地盘不大,但人挤事杂,最让小鸳鸯们头疼的是环境卫生。本来走廊就窄,今天你放一个炉子,明天我扔一张桌子;你向水房倒一些剩饭,我向水房倒一堆垃圾。走廊越来越窄,水房越来越脏,厕所的下水道经常被堵,臭水横流,没两年,“鸳鸯楼”变成了“肮脏楼”。
面对鸳鸯楼脏乱差的面貌,工厂也没少费力气,会开了一次又一次,文件发了一份又一份,管理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说得多,干得少,发牢骚的人多,干实事的人少。就这样,紧一阵、松一阵,好一阵、坏一阵,形成恶性循环。
乱极则治。去年年底“鸳鸯楼”来了一个杨大妈。杨大妈原是一个分厂的党支部书记,在聘任干部时因年龄大而落聘。她“内退”以后来鸳鸯楼照看坐月子的儿媳妇。没呆几天,她就呆不住了。她给家委会写了一个报告,召来李大妈、王大妈、张大妈,成为“鸳鸯楼”的管理人员兼清洁工。大妈们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心中只想为工厂做点实事,为娃娃们办点好事。
她们先制订了一个“十要十不要”的文明公约贴在墙上。白天,从楼里一筐一筐地清运垃圾,晚上挨家挨户地做思想动员工作。起初,小青年们并未把几个老妈子放在眼里,当然也不吃杨大妈的这一套,依然我行我素。杨大妈们讲过理后,仍不见悔改,就照规定罚款,他们不交,中午吃饭时,锅就被提走了,要锅时少不了大妈们的一阵唠叨,一个回合下来,年轻人就不敢碰杨大妈的文明公约了。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没出一个月,“鸳鸯楼”就变样了,“鸳鸯们”也被调动了起来。在杨大妈的统一协调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能耐的出能耐。一阵行动后,厕所通了,墙面刷白了,走廊宽敞了,麻将摊子不见了;楼前多了几副乒乓球案子,楼下还有了一个图书室。今年初,“鸳鸯楼”前又多了一个文明小区的牌子。 (阎冬)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