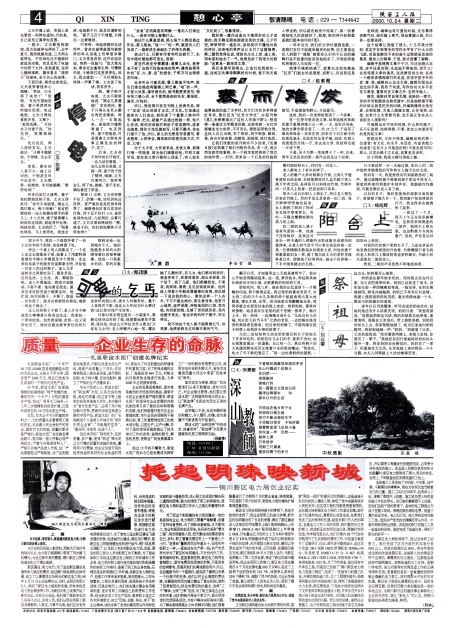表而难发
文/赵紫薇
“发表”在词典里有两解:一是向人们表达什么,一是在刊物上登载什么。
表达什么算是发表,那么每个人都发表过作品。婴儿落地,“哇——”的一声,就是向人们发表了一篇鲜活生命诞生了的伟大诗篇。
表达什么,只要有作者和听众就行了,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发生,容易!
甚至作者还专横霸道:像婴儿出生,皇帝老子来了也挡不住他哇哇的哭声;像有些领导作的“官、大、套、空”的报告,千军万马也得俯首听命。
也有听众刁蛮无理,婴儿落地不吱声,医生们准会提起两腿掴上两巴掌,“哇”的一声,才皆大欢喜。像听报告的,秘书熬更受夜写,领导苦口婆心讲,台下竟愣是些织毛衣、看报纸、谝闲、打盹的。
所以,我觉得只有在刊物上发表作品,那个“发表”说出的话才正式,才文化。它是通过媒体向人们表达。其间多了个重要人物和环节:编辑、把关。就象产品通过检验一样,他不让你说,那你的话就烂到肚子里沤粪吧。读者也随意,楞你天花乱缀地写,只要不翻书,你也打搅不了他。所以,那儿的光景是写者愿写,看者愿看,心领神会,属高级的思想交流方式。可是,太难!
对于大手笔、大作家来说,发表文章,那像打嗝一样随意,因为他们满腹经纶。可我才疏学浅,想发表文章只能呕心沥血了。有人起名“文化民工”,形象得很。
我的第一篇作品是向不满周岁的儿子发表的。我手舞足蹈地朗读完我的文稿,儿子听完,咿咿呀呀一通乱叫,虽然我听不懂他对我的评价,但咯咯的笑声足已支付了这篇稿费。第二篇我觉得还成,便给先生点上烟、递上茶,照本宣科地念了一气,他倒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还算是一篇狗屁文章。”
再后来便呼朋唤友,让他们把我胡吹一通。在相互吹捧得飘飘然的时候,竟不知天高地厚地组织起了文学社。伙计们为社名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定为“红杏文学社”、办起刊物《觅》。赤裸裸道出了这伙人的狼子野心:想觅得一条通往文学殿堂的路,还想有朝一日红杏探墙走出大世界。不可否认,理想是团粘合剂,这伙人自己出钱,买了纸张、刻字钢版、蜡纸、笔,各自开始改稿、刻蜡纸、画插图,挑灯夜战。
让我们欣慰的是刊物有不少读者,《安康日报》还转载了我们刊物的作品。有一次,我去西安医学院看病,在一个病房竟然看到了我们的油印册。一打听,原来是一个石泉的住院病人带去的,所以就在病房中传阅了。那一次看病没吃几次药就好了。我想,那剂神丹妙药就是我们那本油印的《觅》。
一年半功夫,我们的文学社偃旗息鼓,一是我们支付不起越来越多的经费,但主要是这伙人的那个“理想”被那些认识和不认识的编辑们在不经意间给活活地扼杀了。市场经济趁机将我的人马收购一空。
我将手稿都给烧了,就算纪念那些落地“红杏”们逝去的或理想、或野心。但是我还是想写,不是理想和野心,只是想写。
这时,我的一位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位青年想发表文章,结果退稿和草纸在屋子里堆得像小山一样。一天,他告诉母亲,他的文章全部发表了,一共35公斤。于是买了酒肉和母亲一块来庆贺。原来有个识文断字的收废品老头,见他卖的全是手稿,就说:收别人的废纸伍分钱一斤,你这是文章,我就两毛钱一斤收下吧。
于是,母子为第一笔稿费干了一杯。后来,青年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这个故事。
老师说:编辑也有可爱的时候,在你累得快断气时,给你输上氧气,很会掌握火候,所以你一定要坚持。
这个故事让我想了很久,十几年我才悟到:其实并非那青年的写作水平有了什么大的飞跃,而是他锲而不舍的奋斗过程就是发表的最美、最动人的篇章。于是,我才读懂了编辑。
编辑手里锦绣文章千千万,可还是瞪大双眼、多半还是四眼!永远地不停地找,找什么?在找每篇文章的魂灵,在找鲜活的生命,在找一个跋涉者摸爬滚打的足迹,在找字里字外的真、善、美。编辑的心总比天高,编辑的眼光永远比你手高。我终于知道,写作的功夫并不全在文章里,重要的在文章之外:怎样学做人。
确实,编辑经常显得无情,他轻轻一挥手,你的辛苦酝酿就会胎死腹中。但是编辑最可敬的时候也就是把关的时候,好编辑懂得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为他人做嫁衣裳,让你很美。试想,如果什么文章都刊登,岂不是让你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吗?
可编辑也有可怜的时候,什么样的稿子、乐不乐意看,他都得看。不看,你怎么知道你写的是狗屁文章?
想想这些,又好不得意。编辑是我的第一位读者!有文化、有水平、有层次、有鉴赏能力的读者!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不就是想写吗?那么,自发出稿子之日起,就算是发表吧。
出于同情,我把文稿写得很工整。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