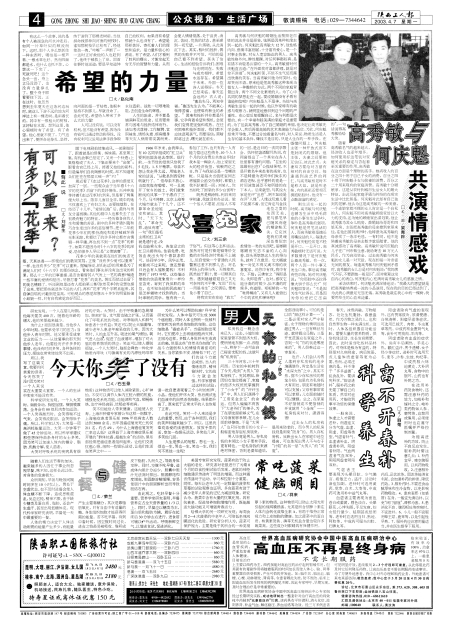
欢喜冤家
□文/刘三余
1966年岁末,由我牵头,有10名同学组成的“红卫兵”要到祖国各地去串联。临行前,一生节俭的母亲只给我了5毛钱,1.5斤粮票。母亲不想让我走得太远,用她老人家的话说,“从乾县到西安转转就行了。”怕母亲不放心,当面我惟有喏喏。可一旦离开了家乡的故土,我们就象断线的风筝一下子漂泊了三个月,马不停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就去了十几个,还不算革命圣地延安和韶山。其时,“天下大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句“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就是通行证,没钱也能乘火车,各地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住宿免费,吃饭由我出头写个借款条即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疯都疯不过来呢,谁还想着日后会有人催帐要钱!不料想到了1973年吧,这些催还借款的信函竟象雪片一样纷至沓来,寄到了我供职的单位,也不知当地的民政部门是怎样辗转才找到我的。当时串联的同学,惟有我一人参加了工作,也只有我一人有能力偿还这些债务。10个人3个月的伙食费总共寄出多钱?我本是一糊涂人,加上家里无大的经济负担,钱粮两讫之日,终了与我却还是一笔糊涂帐。只是每次当值班室同志将催款公函交给我时,都要让我不好意思一回:刘某人,你当初吃了国家的多少白饭呀?
既然是糊涂帐,到后来同学相逢,我就没有办法说。做一个俗人不要紧,但俗人不等于俗气。似这等心态和活法,虽然对钉是钉铆是铆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时常赶不上趟儿,但自觉做一个普通的人民警察还差不到那儿去。对名利场上的得与失,天性使然,既然拙于算计,便一切顺其自然。遇到磕磕碰碰自己又无可奈何的不平事,发回“百无一用是书生”之叹谓后,便难免小看了自己。
将我实实在在地“放大”的一回,是近日的一次同学聚会。执杯把盏酒酣耳热间,有同窗提出了一个其实在各人肚里都有谱的问题:“在坐的谁最有出息?”公推结果呢,不是开着名车来赴宴的高官,也不是特意为老同学们做东的酒店老板,出乎意料的竟是一时间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的在下本人。后来就想,与其说大家是在评“出息”,倒不如说是在评“人缘”。人缘这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肯定与金钱地位之类的东西无关,更与那笔早己随风而逝的糊涂帐无关,它应该是我们灵魂深处类似宗教情结一类的东西吧,是屡颠屡踬而矢志不渝的人心向善。回头再想想这人生的得与失,就有了点意思。它大概就象一对见不得又离不得的欢喜冤家。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错;云佛家之“得即是失,失即是得”,也对:感叹它能分清的时候少,扯不清的时候多,有道理。郑板桥的一句“难得糊涂”,又有几人能悟出个中的玄机和禅味呢?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