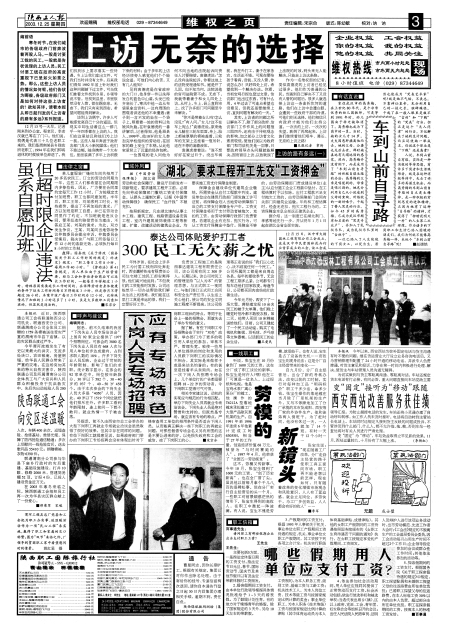
本版导读
上访 无奈的选择
编前语
寒冬时节,在我们城市的各级政府门前奔波着两股人马,一股是讨要工钱的民工,一股就是告状说理的上访人员。民工讨要工钱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已呈如火如荼之势。那么,这些上访人员的情况如何呢,他们告状为哪般,各级政府部门又是如何对待这些上访者的?欲知其详,请看本报从即日起刊发的《上访者的路有多远》系列报道。
12月13号一大早,记者刚来到办公室,程老汉、李老汉就已等在了门口。他们说,我俩是代表三十几位老职工来的,我们是渭南某县乡财政所老职工,1994年在我们即将退休的时候被单位辞退了。我们找到乡上要求落实一些待遇,乡上让我们拿出文件,可我们当时并没有文件。后来我们得知1992年省上针对我们这种问题曾下过文件,可当我们拿着文件找到乡里,乡领导说不管。后找到县里、市里依然没有人管,都在踢皮球。无奈下,我们只有来到西安,希望问题能得到解决。
谈到上访俩字,许多人可能感觉离自己十分的遥远,但现实中却生活着这么一群几乎一年四季都在上访的人,我们在这里姑且称他们为上访一族。这些人每日奔波于政府各部门及大小新闻媒体;他们不修边幅,随身携带一个大布包,里面装满了多年上访积攒下来的材料;由于多年的上访经历使旁人感觉他们个个能说会道。可他们内心的苦,又有几人能知?
见到袁德虎是在省政府的大门口,他身穿一件以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头发已经齐肩长了。寒风中他一边从布袋里拿出资料,一边向周围的围观者讲述他的不幸遭遇;妻子则一言不发的坐在一个袋子上,照看着一地的资料以免被风吹跑。在听袁德虎的一番讲解后,记者得知,他是眉县人,1999年,他10岁的女儿参加完学校组织的劳动后,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车祸,从此他家里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
一位围观的老人问他为何不向当地的法院起诉向责任人讨要赔偿。袁德虎说:“怎么没向法院起诉,你看这地上的法院受理通知书。庭是开了几回,但不知为何,法院说他的官司法院管不成。无奈下,我就带着妻子和女儿四处上访,从村上、乡上、县上直到市上,找了许多部门可问题至今未解决。”
“你不是带着女儿吗?怎么没见?”有人问。“女儿?这不在车上呢么!”袁德虎说。原来她女儿躺在三轮车里面,身上、脸上都被厚厚的棉被盖着,三轮车的支架上还挂着一瓶吊针,还在不停的滴着液体。
袁德虎接着说:“谁不想好好在家过日子。没出车祸前,我在外打工,妻子在家务农,生活还不错。可现在要给孩子看病,没钱,又没人管,你说怎么办?只好四处上访,希望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你看,当初宝鸡日报也登过文章,信访部门也出过东西,可有什么用,4年过去了可连点希望也没看见,但我还是要继续上访,直到问题有解决的一天。”
其实,上访者的问题之所以解决不了,除了部分政府、信访部门工作作风上的问题推三阻四外,还有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之部分上访者文化素质较低,使他们误以为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是一回事,只要政府领导点头问题就能解决。因而盲目上访,以致耽误了上法院的时效,到头来无人能解决,只能走上访这条路。
作为一名维权部的记者,类似袁德虎的上访者已经见过很多。他们作为普通的公民,当遇到自己解决不了又没有人管的问题后,很多人就选择上访这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他们在上访中会遭白眼,会遭到一些政府干部的冷漠,可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相信只有政府才能为他们主持公道。一次次的上访,一次次的失望,跌倒了再爬起来,上访族们继续着他们艰辛、漫长、无奈的上访之路!
■本报记者 章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