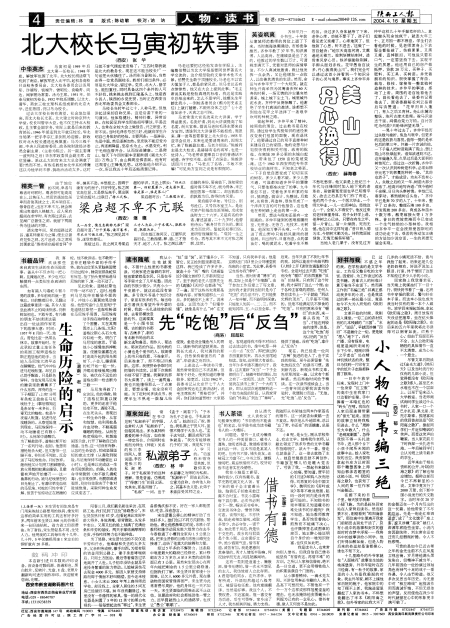
先“吃饱”后“反刍”
(商洛) 屈超耘
我从小生性就爱书,不管什么性质的书都爱读,可我家是在偏僻的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只是在爷爷手里才念了几年私塾,因此存的书很少很少,只有小小一牛皮箱子,就这还远没有装满。多亏我外爷是个知识分子,家里有很多的书。每当母亲引着我去看望外爷外婆的时候,我就一头扎进他家的阁楼,去看那横放竖卧的书。这阁楼真是一个小图书馆哪,古的新的书都有:古的多了,新的有北新书局出的北新文选和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的作品。因为我的小舅也是个爱书的人,故阁楼上的书只准我看,不准拿开。后来准拿了,却不得以旧换新。这样,我便拼命争取时间把借的书读完,以便下次换新书前不留下遗憾。我舅家的那书太深奥了,读上一遍两遍,我也只能懂得那么一丁点意思,要想全懂,完全没有可能。为了赶时间多读点书,我便半生不熟地一鼓脑儿给“肚”里“装”,至于懂多少,不管它,反正捡到篮里都是菜。这样,我已经读了许多许多,就连十分“别”嘴的《读通鉴论》《佩文韵府》几乎都浏览过了,至于我的老先人屈原先生的《离骚》《天问》也都通“吃”了一遍。至于这些书究竟都是些啥内容,好像知道那么一点点,多的就说不上来了。说来也怪,正因为这个“似懂非懂”,就像是有什么“神”在支使我,愈是没全懂愈吊人的胃口,读新书的欲望就更高。直到长大成人,我对遇到的新书,仍然保持着强烈的“读欲”,毕欲读之而后快。
上述这么一种读书习惯,虽然常常使自己不求甚解,但却有个好处,使我知道的事情较多、较宽泛。比如1962年,县委书记从北京开七千人大会回来传达毛主席讲话时,说毛主席批判“贾桂哲学”,并问:你们谁知道贾桂?大家都不知道,只有我举手说:他是京剧《法门寺》里公公刘瑾堂前站班的小宦官。为此事,县委书记当场夸我“博学”。
当然,彼时所谓“博学”的我,实际上仅是个“半瓶醋”。由于参加工作后爱上了写文章,这时我才意识到当初只是为了“吃饱”的办法不行,它只能使人一知半解,而不能明其深意;只能使人知其一、二、三,而不能知其四、五、六以至全部。于是,客观逼得我不得不对自己过去读过的书,像牛吃草一样一点一点“反刍”,即把读过的东西重新找来,再从头至尾地细读。谁知,这样做大有益处。当年许多半通不通的句子、段落,这次重新“反刍”一下子全都明白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之有了一定阅历,这次“反刍”使我在读书上来了一个大的飞跃,即从浅层次地理解到达一个较为高级的阶段,从我家背后的“终南山”到达了“秦岭”。后来,当年只读了不到七年书的我,其所以能在中央级刊物《人物》上开《读资治通鉴新论》专栏,全是对过去只图“吃饱”而没有“嚼烂”的东西重新“反刍”的结果。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深明了这么一个理: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任何人想在读书上一下子就能“到达光辉的顶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绝不能满足饥不择食的“吃饱”。只有把原来没有“嚼烂”的东西,来一番从容地“反刍”,才能达到较高的境界。但是,这个先“吃饱”却为以后的“反刍”提供了基础。没有“吃饱”,拿什么“反刍”?
现在,我已经是一位向“古稀”挺进的老人了,由于实践的经验,至今还保留着“先吃饱后反刍”的读书习惯。遇到新内容、新观点书和文章,先草草浏览一遍,以求有个新鲜感。然后再抽时间给予精读。在一次读书座谈会上,当一些青年同志要我谈读书经验时,我便脱口而出:“无他,先‘吃饱’,后‘反刍’”。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