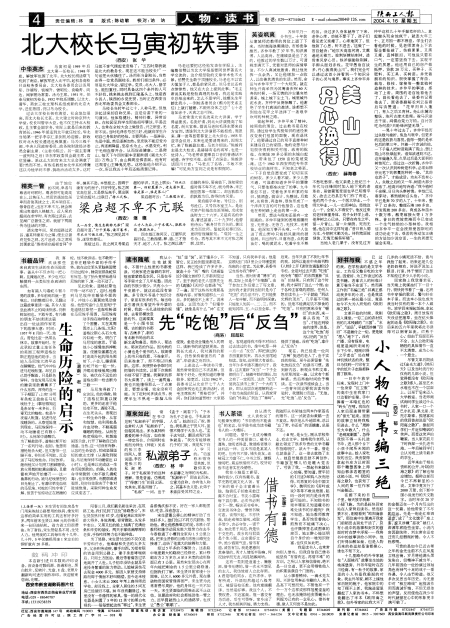
小人物的“韦编三绝”
(西安) 郁文
已过不惑之年的我,在学校读的是文学专业,工作后又整日吃的文字饭,因爱好、为工作读过的各类书籍,若拿古人的标准计算万卷当不在话下。然而真正作到“韦编三绝”并真正感动我多年的小说,也是我读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竟是如今不大为人所知的《欧阳海之歌》。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刚迈入课堂。一穷二白的农村仅有的几本残破的“三国”、“水浒”、“说岳”,早就因涉嫌“四旧”不是被付之一炬,便是被“埋入”地下了。没有广播、没有报章,电视更是闻所未闻的乡下少年,刚刚识得“之乎者也”处在精神饥饿状态的我,整日为找到一片印有文字的纸片子走路都睁圆了眼珠。
一日中午放学归来,发现村上门中一位身穿“红卫服”的高中生在我家门口边看护庄稼,手中捧着一本暗红色的“砖头”在啃。我站在人家后面连猜带蒙的“借光”起来。里面的故事立刻将我吸引进去,什么“周排长火中救人”,什么“老鸹窝剿匪”,急得我恨不得一头扎进书中,进入那个乡下小孩子闻所未闻的故事中去。趁人家吃饭的当空,我贪婪得拿起书皮方以封面那个雕塑图象上得知由郭沫若题签的这部小说,叫《欧阳海之歌》,也获知了人间的第一位作家叫金敬迈。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天放学我都小腿飞跑,为的是赶快回家站在人家背后读书。然而好景不长,刚刚看到“欧阳海参军”,那位高中生便离开我家门前稻田去别处干活了,只有小说中的故事和封页的画面时时在梦中浮现……我将书中的故事讲给小同学,他们听得如醉如痴,但是人物后来的命运却是谁都揪心,谁也不知下文。
十几里路外的外爷家就在“人面桃花”故事发生地的桃溪堡旁,外爷年轻时在四川经商,有一肚子的故事,家里的小人书是我垂涎的对象。我去外爷家,顾不上摘他家后院的桃子,他家院中的知了顾不上抓,我跑进屋里翻起了人家的书本。不料想竟翻出了半本《欧阳海之歌》。但外爷家的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小姨死活不给,竟与我抢了起来,后来还是几位老奶奶相劝,好说歹说加上眼泪、打滚,终于借回了这部不知经过多少人手的小说。
回家路上我欣喜若狂,当天晚上我煤油灯下一目十行,很快将书看了一遍,还将书中穿插的歌词、警句抄在本子里。而这本小说也成为我当时仅有的第一本个人藏书。放学回来端起饭碗,拿起《欧阳海之歌》,周日放假雨天没法挖猪草,坐在炕头捧起的还是《欧阳海之歌》。在后来的五六年里我将此书读得可以倒背如流,烂熟于心。’但由于后面页码不全,主人公欧阳海牺牲的具体情节一直不太清楚,成为心头一个悬念。
尽管文革后期读过《金光大道》、《艳阳天》以及当时流行的仅有的几部小说,但觉得都没有《欧阳海之歌》感人,甚至艺术水准也不在一个层面上。以至于后来迈入大学教室,当老师测试询问学生读过什么书时,人家一口一个巴尔扎克、果戈里、老托尔斯泰,孤陋寡闻的我回答却说是“《欧阳海之歌》”,激起同学们一片近似嘲讽的笑声。而受这笑声的鞭策,当人家花前月下时我却一头扎进书海,一年后被同学们公认为班上读书最多的学生。
近年来由于相关资料的公开,对《欧阳海之歌》的了解也相应增加。据称这部而今已不再彰显的小说,文革中竟发行了2000万册,创下新中国小说发行的天文数字。当时年仅28岁的金敬迈在一个月内写出的这一长篇,给他带来了不尽的厄运。先是一炮走红奉调进京,成了“文化旗手”座上客,旋又涉嫌“恶攻”被打入深渊牢底险些坐穿。小说内容因副统帅、刘主席命运变迁而几经删削折腾,令人不胜感喟。
可贵的是如今已近古稀之年的金先生前不久在凤凰卫视出镜,岁月将他满头黑发染白,但精神不减当年。几年前因给一位扮演过领袖角色而神气十足的戏子一番冷遇,令人击节称道。他又多次反思当年历史,为无意中对“极左路线”起推波作用而真诚忏悔,不但无损他的声望,反而使他在我少年时代就留在心中的形象更丰满可敬了。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