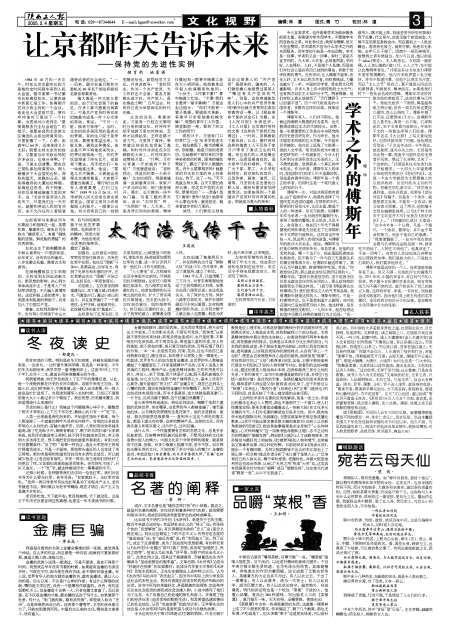
名著的阐释
·老柯·
或许,文学名著也是“随你怎样打扮”的小姑娘。换言之,就是对名著的阐释,亦往往折射着某种时代色彩、政治需要和现实功利,抑或因其阅读角度差异出的或岭或峰来。
比如成书于明代中叶的《水浒传》,单是关于它的主题,数百年来就众说纷纭:有匡扶社会正义的“侠义”说;有张扬个性的“思想解放”说;有反讽朝廷失政的“忠义”说(盖忠义既在梁山,则反证出朝廷上下的不忠不义);有持否定态度的“诲淫诲盗”说;有“造反有理”说;有“农民起义”说。到了近代,或出于反清需要,或为了回应彼时思想新潮,有的研究者从《水浒传》中发掘出“排外(族)”思想,或发现“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甚至认为此书是“讲平等、均财产的社会主义小说”。此类比附之说,因其过于离谱离奇,而被鲁迅先生当年嘲讽为“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文革后期,《水浒传》又成为“好就好在投降”的反面教材。近读当代学者王学泰的《水浒传》思想本质新论,王先生在梳理出上述种种之说后,认为《水浒传》写的并非“农民起义”,因为书中实际上很少涉及宗法社会的农民生活,更没有表现出宗法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的诉求。该书中所写的英雄好汉,多是脱离宗法网络、宗法秩序沉沦在社会底层的游民或社会边缘人物。小说中描写了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的挣扎和奋斗。并表现了他们的经济诉求(追求优裕的物质生活),和其希望迅速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发迹变泰”的政治诉求。王学泰先生的结论是:《水浒传》所写的是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
手头还有份关于探讨《西游记》主题的剪报。作者王振宇教授是位心理学家,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颇有研究。按照弗氏学说,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构成。本我是精神结构中最古老的生命核心,由爱欲和破坏两种本能构成,具有潜意识的特点。自我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部分。与本我的放纵欲望,易于原始本能冲动相比,自我已具有控制本能、趋利避害,以实现自我保存的理性特点。从自我“再上一个台阶”,便是由自我理想和良心组成的超我。超我虽是“晚辈”,对自我却往往以“父母”(教育者)自居。如是,王振宇教授拿弗氏理论与《西游记》里的人物和情节对应,他看到的这部神魔小说,描述的便是人格结构中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之间的关系、斗争和演变了。如书中的唐僧是超我的代表,孙悟空(包括八戒和沙僧)是自我的形象,各路妖魔鬼怪则是本我的体现,佛和菩萨不消说是父母(教育者)的化身了。至于孙悟空从“妖猴”(本我也)、“取经行者”(自我也)到“正果”(超我也)的不同阶段,自是反映了个体心理发展的全部历程。
上边两位学者对名著的反传统解读,虽是一家之言,所提出的看法也未必人人赞同,却也不啻洞开了一个窗口,使人们惊喜地发现:原来名著里还藏着这么一块新大陆!在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人们对名著的解读也日呈多元性。其中,既有纯学术性的摒除功利,另辟蹊径,力图突破某种思维定势或僵化教条,以求尽可能还原名著思想主题的真面目(如有人从宗教角度剖析《西游记》,指出其叙事框架是完全受制于“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这一宗教考验母题和主题),亦不乏功利目的明确的“借题发挥”。例如把《三国》与人才战略相联系,把孙悟空与最好员工相挂钩。《红楼梦》里的人物和情节,也常被杂父家拿来说事,用以针砭时弊。日前坊间有本《闲读水浒》,提出一个有趣问题:为何父韬武略皆不出众的宋江却坐上了梁山第一把交椅?缘此作者分析了宋江善于笼络人心,广泛培育自己的人脉关系,精于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并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政治资源,从而以“无用之用”终成“大用”矣。这类具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阐释”或曰“借题发挥”,往往使当代读者“眼前一亮”,从中不无获益了。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