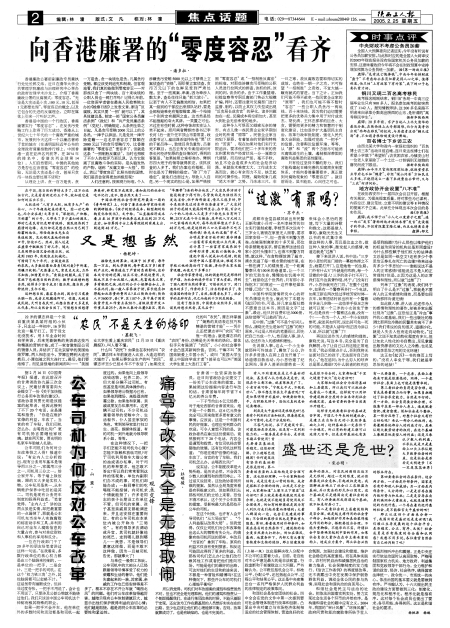
“过激”有罪吗?
·苏中杰·
成都市金堂县城郊派出所民警王新和黄小兵对一名叫李桂芳的妇女实行强制戒毒,李桂芳多次说有个三岁女儿被锁在家里无人照看,要求回家安排一下,但一直得不到警方恩准。在被强制离家的十多天里,那位母亲曾跪地哀求,曾在被押送途经自家小区时头撞车门,也得不到警方同情。就这样,“在食物摆放满了超市、清水充溢了每一根水管的城市里,在一栋住满了人的楼房里,在一个距离警察只有100米的巷道里,让一个三岁的无助生命,慢慢地在饥渴中死去”,她留给这个世界的,只有那小手指抠木门的痕迹……这件事经媒体传播,已经广为人知。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康晓光先生,就此写了本题为《起诉》的书。可是,好几家出版社都不愿意出这本书,原因是文字“过激”。最近,他只好自费印出3000册,送给觉得“可以救药”的人。
在中国,“过激”可不是个好词儿。那么,康晓光先生是如何“过激”的呢?原来,不过是人性化的笔墨而已,即先把自己当成一个人,然后做人事,讲人话,论述作为人的感情和理性。
先说做人事。这么一个小生命就那样可怜地走了,震惊了公众,许许多多普通人在网上自发开展了一场道德自救活动,为小思怡建了纪念网站,很多人甚至自愿绝食一天来体会小思怡的困境,写下大量的诗歌和挽文。这都是做人事的。康晓光先生又以书的形式集中来做这样的人事,而且是泣血之作。做这种人做的事,激发起人的感情,难道这就是“过激”!
接下来说讲人话。书中说:“三岁的小思怡死在门前的一幕始终挥之不去。她要打开门,这是她惟一的生路。门外有什么?门外就是你和我,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三岁的孩子打不开门,我们在外边装聋作哑。终于,门没有打开,小思怡就死在门后。”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警察再多打一个电话,如果王新在两次经过李桂芳家时停一次车,如果团结村派出所有一个警察肯多走几步路……这些举手投足之劳就可以使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免于惨死,但是没有一个警察这么做,没有一个!一一作为一个人,对一个小女孩的惨死,叙述其如何死,说出其可免一死的可能,不是讲人话吗?而正因为讲以人话,所以就“过激”了!
再说论述作为人的感情和理性。康晓光说,写这本书,完全是为了自我解脱,为了让自己以后还能正常地生活,“我必须做点什么,否则我将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他在追问:为什么穷人的呼声总是那么微弱?为什么弱者的权利总是受到践踏?为什么那些以维护他们的权益为宗旨的机构总是形同虚设?为什么那些赋予他们权力的法律条文总是如同一纸空文?还有多少个李思怡正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将来还会有多少个李思怡?——谁能说这不是人的正常感情?谁能说这不是人的正常理性?但是,正因为这是人的正常感情和理性,所以就“过激”了!
列举了“过激”的表现,我们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不“过激”。那就是不要有人的正常感情和理性,而是要如同动物那样冷漠无情!
如此做人事、讲人话、论述作为人的感情和理性的著作,却被多家出版社视为“过激”,这恐怕正是“冷血”事件的心理基础,我们一些出版社的格调比那两位冷酷的民警其实高不了多少!我们常说的良知泯灭、道德沙化,就是人失去人性而走向动物化。“过激”之说不知其动物化程度有多大,但让如此人性化的书自费出,足见掌握出版资源者的文化人之冷酷,也足见形成李思怡之死的文化环境!
这正如《起诉》一书的扉页上写的:“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