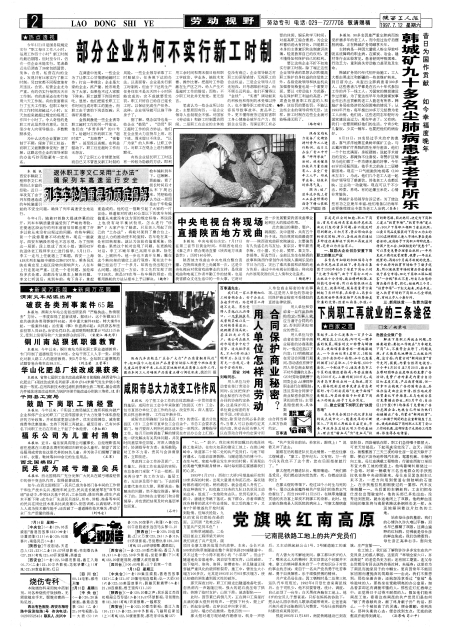
本版导读
觉旗映红南高原
——记南昆铁路工地上的共产党员们
“七·一”前夕,我们来到举国瞩目的南昆铁路工地采访。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工地上,在崇山峻岭中,铁道部二十局二处的共产党员们,与地下暗河涌水,与溶岩溶洞裂隙,与隧道塌方的搏斗中,在生与死、家庭与事业发生冲突的时候,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慨和献身精神,每时每刻都在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1993年1月17日,西街口大桥3号墩基础开挖到10米多深的时候,出现大量涌水和泥石流,基坑随时都有塌的可能,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人身伤亡。在这种情况下,担负施工任务的九队13名党员主动站出来,组成了一支抢险突击队。党员毛家礼、孙跟斗、唐建光等跳下基坑,换下群众,赤着双脚在冰冷刺骨的泥水中作业排险。在之后的施工中,又有7个桥墩基坑开挖时遇到险情。但每次抢险,九队的党员们都抢在最前面。正所谓“危难之际,方显共产党员本色”!
在秧草地隧道,二处项目部总工程师梁天祥向我们讲述了共产党员、副项目长廖太煜苦战塌方的故事。本来,全长不足500米的秧草地隧道在整个南昆铁路250座隧道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弟弟”。但由于隧道地处岩溶地带,因岩层节理发育,山体破碎,地下暗河、溶沟、溶洞、溶槽密布,并且隧道正线穿越严重风化的破碎断裂带。施工中,曾发生大小塌方100多次。尤其是1993年10月9日那次塌方,使已初砌的洞体遭到毁灭性的破环。
那天深夜12时,职工们刚走出隧道准备吃饭,忽然洞内一声轰隆巨响,强大的泥石流压弯了拱排,挤跨了临时支护,山体下滑,地表裂陷……
此时,因劳累已病倒几天,正在洞口工房里打点滴的廖太煜听到响声,一把拔下针头,提上矿灯,抓起安全帽,边穿衣边冲向掌子面。
这时,塌方仍在继续,危机四伏……
廖太煜对塌方现场略作勘察后,转身一声怒吼: “共产党员往前站,抄家伙,跟我上!”说着又冲了进去。
紧跟在后的掘进队长见此情景,一把拉住廖太煜喊道:“廖工,您年纪大,又有病,万一有个闪失我负不了这个责,您在后面指挥就行了。”
廖太煜甩开掘进队长,嘴里嚷道:“我们都是党员,我们都应该向党负责,死,伤都应该是我们!”
在廖太煜的带领下,经过32个小时生与死的搏斗,塌方这条恶魔终被共产党员们的浩然正气给震住了。而当1993年11月15日,在秧草地隧道贯通的庆功宴上却找不到廖工的身影。此时,他正躺在路南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可廖太煜病愈后,又主动挑起赵公山1号、2号隧道施工的重担。
有人曾大为不解地发问:廖工都50多岁的人了,哪来这么大的精神?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廖工的精神源泉来自于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来自于一名共产党员勇于吃苦奉献,勇于自我牺牲,乐于顽强拼搏的精神。
共产党员母仕彦,因工牺牲时是二处第三机运队汽车班班长。1992年6月母仕彦来南昆线后,由于司机少,他不仅要管理、统计、调度,自己还顶了一台车,白天黑夜奔跑在工地上。他3岁的宝贝儿子想爸爸,只好在妈妈的协助下,把从幼儿园学来的儿歌录成磁带寄来,让爸爸高兴高兴或许还能换回几句赞赏。可母仕彦到临终时都没有来得及听。
那是1993年11月18日,南昆铁路建设已到攻坚阶段,西段铺轨在即。职工们急得嗓子眼冒火,可老天给捣乱,下起雨来没完没了。这天,雨刚住,被整整困了三天三夜的母仕彦一见老天睁开了眼,便迫不及待地带领汽车班,驾着机械、车辆冲向工地。母仕彦满载工程物资,行驶在西街口至雨布宜大桥工地的便道上,他鸣着喇叭刚绕过一个急弯,对面一辆载有三名当地群众的手扶拖拉机在路中央迎面驶来。母仕彦见紧急刹车已来不及,一把方向甩到便道右侧陡峭的石壁上,在手扶拖拉机刚刚驶过的一霎那,汽车反弹侧翻……。当后面的车辆赶到,工友们把母仕彦拉出驾驶室时,他的头部已多处出血,没等送到医院,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他的鲜血连同他的躯体将与南昆铁路这条钢铁长龙一样,永远地浸润着这片红色的土地。
站在母仕彦的墓前,我们的心情许久许久难以平静,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这满山遍野的红杜鹃,仿佛就是母仕彦的鲜血染成;我们仿佛看到,母仕彦正高举右手,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在工地上,我们还了解到许许多多发生在共产党员身上的感人事迹。这里有“率领全家六口,齐战南昆”的老党员史方前;还有因工期紧,连父母去世都没有回去送终的杨汝林、朱福寿;这里有为了南昆而抛家别子的巾帼女,更有因常年不能回家团圆而遭抛弃的筑路郎……由此,我们不禁想到,那些坐着吉普,还抱怨没享受过“皇冠”是啥滋味的人,那些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细品香茶却还有满腹牢骚的人,那些在灯红酒绿之中,还觉得日子过得不耐烦的人,假如他们能来南昆工地,看看这些南昆的共产党员们是如何“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话,那么,一个个被扭曲了的灵魂,便会震颤,受到洗礼,那种失衡的心态,便会找到支点,无底的欲壑或许能得到满足。 (孙厚鸣 苟小平)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