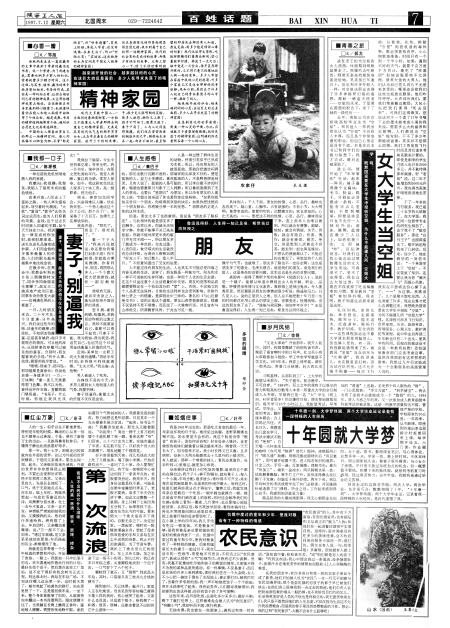饥饿中度过的童年和少年,使我对粮食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
农民意识
文/叶平
我是1961年出生的,那是吃大食堂的最后一年。母亲说怀我的日子里,她没见过油腥,连野菜稀粥也喝不饱,奶水更是不会有的,我这个胎里没带“粮食”的孩子,该如何活命呢?好在母亲人缘好,食堂做饭的姐妹们就偷着从锅边盛来米汤,喂着我一天天长大了。因为营养不足,我小时长得又丑又瘦,且多病疾,母亲三天两头抱着我去十几里外的小镇求医,有人就说:那样一个难看的娃儿,看的还真值价。母亲听到,心里难过,就更加心疼我。
母亲曾讲过我们小时吃饭的情景:姐弟四五个都站在锅台边,我个子小,够不到锅台,就站凳子上,每人一个小碗,平均分配,谁多谁少,常吵得不可开交,其实每次是我碗里最多,也是我的吵闹声最大。每到这时,姐姐们就再给我分点才得安宁。懂事之后,我就发现母亲总是最后一个吃饭,一碗半碗也就揍合一顿。她总是食尽我们洒在桌上的饭粒,有时还会舔净我们的空碗;在路上看到一穗麦、几片菜叶,也总要细心地捡拾回家。从那以后,每当我放学回家,看到冰锅冷灶,再也不哭闹着向刚从地里回来,脸上挂着汗珠的母亲要饭吃了。在小镇上学的四年间,我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不是粮食不够,是我背着母亲总要把她给我装好的粮食再放下一点。饥饿中度过的童年和少年,使我对粮食有了一种特别的情感。后来和城里长大的妻子一起过日子,我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常使她不可思议,不但讥之以“农民意识”,甚或从那些“小气”的细节中,对我有过不少误解。然而,我毫不犹豫地吃尽她和孩子的剩饭的情形,又使她不得不为我的某种品质所感动。有一件事情,不仅是妻子,而且是在场的许多人受到感染。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大杂院,女儿不小心把一碗饺子倒在了水泥地上,妻正要打扫,被我拦住了,当着许多邻居的面,我一声不响地把饺子一个个拾起,用开水洗净吃了起来。没有讪笑声,人们都夸我做得对,我却感到应该这样做,好好的饺子扔了多可惜啊!
这些年来,在外面吃饭,总是吃多少买多少,最好不剩,剩下了就打包带上。这样做难免会被人讥为“农民意识”、“穷酸小气”,我却听而不闻,我行我素。
无独有偶,我也曾在一些酒宴上,遇到过和我一样有“农民意识”的人,其中有千万富翁,有部长级官员,也有画坛和文坛真正的“腕儿”人物,和他们在一起进餐饮酒很平实很自然。退席时,面对满桌没有吃多少的美味佳肴,会不约而同地向服务小姐说一声:请打包。偶尔也有人说一句:别带啦!多麻烦。很快就有人接上话:“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或“咱们都是穷人的孩子嘛!”听到这些话,我心中便会淌过一条溪流,母亲饿着肚子,流着汗水在地里劳作的情景如在眼前,让人心里酸酸的难受。
在我的朋友中,有许多昔日和我一样的农家子弟如今成了新贵,他们只怕被人饥为“农民”,一言一行无不刻意与农民划清界线,那个饱尝饥饿的穷孩子的影子早已被他们淡忘,在他们身上很难找到一点过去的痕迹,他们中有人会把奶油面包象扔烟头一般扔掉,也不肯给饥目灼灼的乞儿。生活得更美好是人类的天性也是终极目的,我无意责难朋友们,我只是不敢苟同他们的人生态度,不仅仅因为生活还不允许我浪费粮食,而是我的骨子里没有浪费粮食的习性。想必,我的这种“农民意识”,大概不会有什么耻辱吧!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