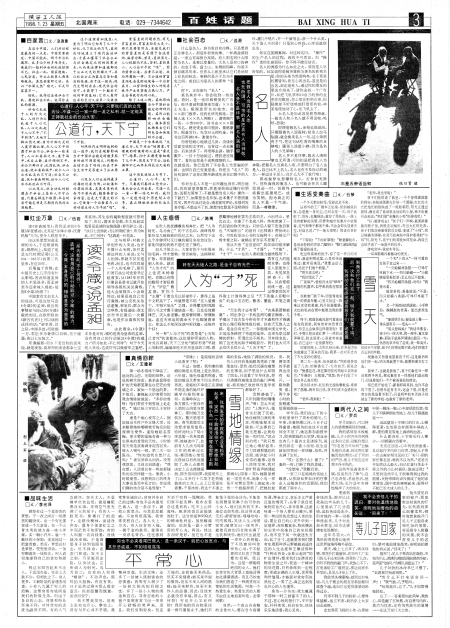她像小鸟一样张开双臂在雪野上跑起来,突然一个趔趄滑倒了。把她拉起来,我俩发烫的手就再也没有松开。
雪地情缘
文/王建新
第一场冬雪终于降临了。远处的山峦、无垠的田野,近处的树木房舍,甚至连显得空旷的天穹都笼罩在白茫茫的雪域之中,寂如一个悠远的梦。午饭后,妻拽起火炉旁看书的我含情脉脉地说:“多好的雪呵!咱们带孩子到雪地上走走吧。”她已给三岁的儿子穿好了大衣。
妻是个痴心爱雪之人,据说她出生时户外正降大雪,母亲瞅着她粉嘟嘟艳若梅花的脸庞顿生爱怜,遂给她起名雪梅。更主要的是她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爱雪的天性。小时候雪天常是滚着满身泥雪回来,被大人喝叱一顿,第二天一如既往。“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妻突然仰头问我,没等我回答,又自言自语道:“我在想,人活着总有一些如影随形的东西伴随一生,像我,小时候爱雪,没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也是雪中私订的,你说我们俩的结合是不是雪缘?”
“雪缘?!是琼瑶的言情小说看多了吧!”
不过,细想,我和妻的婚姻的确是从雪地上走出来的。六年前,她生母溘然病逝,续弦的继母又带来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家庭的不幸使正在省城外院走读的她只好辍学内招到林业局,在秦岭深山一条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的山沟里当营林工。那时她万念俱灰,整天愁眉不展,春节放假后主动要求留场值班,恰好此时山下局小学急需一名英语教师,她被选中了。此前有人几次为局部工作的我牵过红线,都因她心绪低沉借故以后再说推脱了。经人点拨我决定上山去接她报到。那天雪雨初霁,我搭班车上了山,又步行十几里才赶到她值班的工点上。山上已是银妆素裹,千里冰封。我这个不速之客的来临,她除了满脸的惊讶,引人注目的是她眼角凭添了缕缕鱼纹,显然,她仍沉溺在痛楚的往事里。似乎想说什么却咽了回去,只说累了早早休息。翌日清晨我被她急促的敲门声唤起,原来她已收拾停当连早饭都做好了。
雪野静极了,只听到踏雪的嘎嘎声。“喂!怎么不说话?”上路不久,她首先打破了沉寂。她说她明白我的来意,昨晚她根本没睡着,可这事自己毫无把握,让我给她一些时间。“说点别的吧!”我只想让她心情好起来,尽力回避那尴尬的话题。她讲起小时爱雪的趣事,逗得人阵阵发笑。我对着旷野高声朗诵起那阙《沁园春·雪》,她眼里燃起一团亮光来,她象小鸟一样张开双臂在雪野上跑起来,突然一个趔趄滑倒了。把她拉起来,我俩发烫的手就再也没有松开。一路欢歌笑语,两个多小时的旅程感觉很短很短……
半年后,我们在山下的小学校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年来,夫妻相濡以沫,小日子过得蜜甜,她眼角的鱼纹不在意间全不见了。她还参加函授学习,即将圆她的大学梦,我业余也有几十篇诗文见诸报刊。虽然仍挤在一套小房里,但生活就如同雪地一样恬静、坦然,并充满了生机。
“哎!还想什么?傻了?”妻的一肘,打断了我的思绪。
“没想啥。”我敷衍着。
一家三口在绵绵的雪地上踱着,从那段如梦如诗的往事走人这幅美妙的雪景图,我们都成了画中人。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