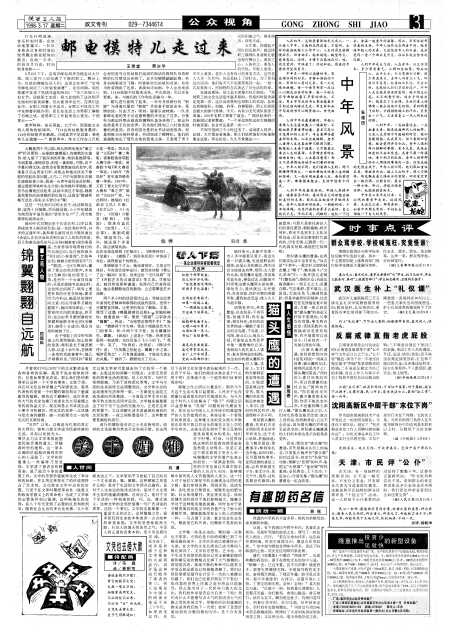
本版导读
关于媚雅
刘谦
尽管我们可以对时下的文化繁荣会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甚至于完全相悖的评价,但是如果要说真话,那么我们恐怕都得承认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文胜于质,并且对文坛这种浮靡之气深感忧虑。最具代表性的是前一个时期的媚俗和目下愈演愈烈的媚雅。媚俗达于巅峰时,连许多卓有大气的名家也操刀或者化名大写黄赌之类的高效益文字,现在则是从书本或生活小事中寻些题目,西化式的卖弄一点风骚与低水准的幽默,搞一点轻薄为文一地鸡毛式的支离怪诞。
“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真正的大师们,曾努力使文学成为民族性格的主流,并加以发扬光大,竭尽全力让文学承担起塑造民族灵魂的道义。但随着时世的推移,这一原本正确的价值取向被别有用心的人歪曲了,文学的价值重心一再偏移乃至变异,文学成了意识态的晴雨表,成了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文学的思想价值被异化成了革命性的标帜,并且用这种异化了的价值观挤占了艺术性、文化性在文学中应有的位置。乃至于在文革时期把革命性(狭意义的政治学意义上的革命性)当成了文学家的必要条件加以强调。这种极端化的变异,在八十年代受到了必要的反思和批判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发展,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却可悲地走向了它的另一个极端,主张过份的消解一切观念,主张无思想性的简单生活的再现,私人化写作,与时代保持距离,乃至于恶性西化等等。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始终无法调整到位。文学和生活的运动速率无法保持一致。一方面是生活的主流加速向市场靠拢,一方面是文学本身日益排斥和主流生活同步运动。文学越来越暴露出了对于当下生活的无能为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太过消解生活本质涵意的通俗的生活场景,一夜之间粉墨登场了。这种繁荣便是媚俗的流行。
流行的媚俗是有识之士无法接受的,政府的文化政策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管。在这两面夹击之下,文学家似乎又拾起了自己的另一个文化面具:雅,媚雅。这种媚雅之风是什么呢?是对于生活的文字西点式播花,是对于人生命运的肤浅式诗化,是对于大众艰辛生存的逃避或憧憬,总而言之,是对于当下生活的一种刻意的轻、巧、浅、薄式演义,这种文学的全部价值像一句广告词说的那样:还你一个梦幻。文学的全部都像一个童话大王的总汇。这种媚雅之作,最多回归到生命的本体或者一点点纯粹的审美体验,文学的思想性隐然无踪,只见人间烟火的浓烈之气,不见人间正道的沧桑本相,更不用说质问灵魂,点化生命了。或许是有感于这种文学现象的大面积流行,或许是这种流行败坏了读者的胃口,有人说现如今中国人的阅读水准远不如三十年代。如果真是这样,在目下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下一代,在若干年后,他们的阅读水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我们反省的现实吗?
媚雅之作之所以大量走红,固然与今天这个生活水准日益提高,人民对于生存质量日益欲望化的时代氛围有关,与今天这个时代人们在解决了“肠子”问题之后日益想解决“灵魂”问题的时代潮流有关,其实也与中国人人文传统中的渴望尊严的人生价值观有关。其实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是,这种雅文化的受众绝大多数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现在正在上学的学生有关。这些生活在相对于其父兄辈明显优裕现实中的受众,他们对于时髦、时尚,与世界接轨这样的价值指向接受起来显然要主动得多,但是正是这个现实原因才更令人对一味媚雅的文学价值产生真正的担忧。一项调查表明,现在的中学生读过古典中国名著的人仅占0.03%,能够理解中国传统人文价值观的人更少。这一代人对于他们父辈坚守的正确观念认同的是少数,他们穿则名牌,用则洋货,说话发嗲,连吃饭也日渐西化。媚雅形态的肥皂剧、妇女休闲期刊,美容美发杂志、休闲保健生活时尚对于他们影响极大。媚雅文学对于这种现实推波助澜,同时也对于坚守精英取向的纯文学的价值产生了极大的消解作用。媚雅就像浮在女人脸上的面膜一样,一旦占据了主流,就会完全失去生气。精致是它的外表,但精致不是美的本质。
文学雅一些是应该的,哪怕媚一点雅也不要紧,可怕的是日前的媚雅已到了为雅而雅的地步,文学的价值已被雅挤出了主流。在文学的文化品质也已成为雅的人格化面具了。文学的思想性、艺术性、对于生活本质探究的取向已完全被雅前面的媚和媚后面的雅格式化掉了大气雄健的,深刻宽容的,崇高平静的种种可以滋养文学受众的品质也已经被雅消解了。我们已经经常看见报刊在讨论下一代的人格健全问题了,我们也已经意识到在下个世纪一体化着的世界上民族之竞争将会日趋激烈,那么做为对下一代影响力极大的文化,我们的作家是否应当自省一下呢?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写点大气的俗或者大气的雅之类的休闲文字,用精致的俗和雄健的雅来滋养我们的下一代呢?放弃了思想价值烛照的为雅而雅的写作,是十分有害的。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