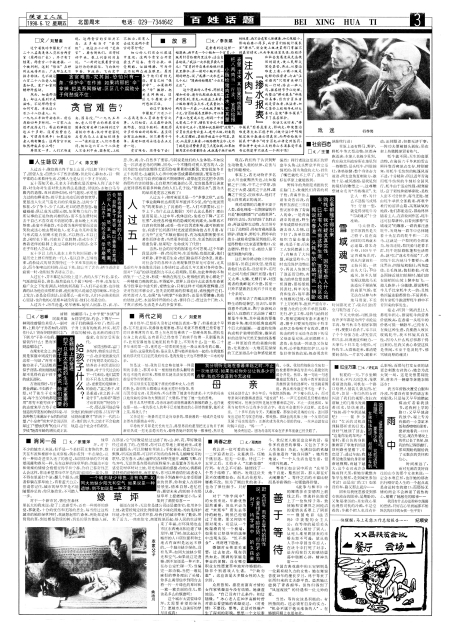
我分明听见她在垂暮来临之时,不止一次地感叹:如果当初你外公让我多少识点字,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样。
母亲
文/刘爱玲
离乡经年,已经好久没有过对她认真地一瞥了,但是在这个早晨,在不经意间,我静静地观察她,那从来就不曾梳理已经带卷了的日渐稀薄的白发,那土灰色的仿佛结了一层硬壳的脸,胡乱挂在身上的衣服。还有那只已经变形了的病手仿佛一只驯服的羔羊,此刻安静地依在她肮脏的外套上。不知为什么,这一刻,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竟对这一切顷刻间生出一股从来没有的心酸。
是的,这是我的母亲,是从没人愿与她并肩站在一起的,在我做新娘的那天仍兀自诅咒我的母亲,是我发烧七天也不曾喂我一口水的母亲。
但是这一刻,我的目光定格在她羊一样温顺的手指上,那其中有一根细细的指头翻转着再也不能弯曲回来,那根原本就无法反抗的病指是劳作时折断的。
其实母亲实在是属于漂亮的那种女人,白皙的肤色,清彻的大眼睛从来就无需任何修饰。然而因为是女孩,又因病残,外公拒绝了她读书的请求,十六岁的母亲以她残缺的身体为大舅换回了大舅妈,开始了她一生的苦难。
腊月北风呼啸着,母亲冰凉的泪悄然滴落在新嫁的路上。也许就在那一刻,一枚仇恨女人的种子已在她荒凉的心田悄悄萌芽。她祈求上苍:赐我儿子!
父亲是在一场暴雨过后走向母亲的,那浪漫的一刻或许是被母亲漂亮的眼睛击中的。
平稳的岁月却是长长的无言。渴望男孩的愿望把无言的日子渐渐炽热成一把无法熄灭的火,燎烤着她纤弱的每一根神经。然后是我、小妹。我们的相继出生宛如一枚枚重磅炸弹在母亲内心最脆弱的部分开花。然后,她一句比一句恶毒地诅咒我们。在我十四岁面临是否继续读书的选择时,母亲跳着脚说,我从来没读过书不也一辈子,女娃还读什么?多少年后,当我经历阵痛,产下瘦小的儿子,而对母亲询问的眼睛故意说“是女孩”时,一声冗长的叹息仍梗在她枯瘦的喉间。但我分明听见她在垂暮来临之时,不止一次地感叹,如果当初你外公让我多少识点字,我也不会落到今大这样。这是母亲。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天翻地覆,那惊动我灵魂的白发,连同那发出过诅咒与叹息的唇,那残指,那缺血的肌体上每一个反常的却又属于母亲的动作,正渐次成为我内心里的灼痛。一丝冲动就在这时脱口而出:“妈——”。
她没有回应,因为母亲的耳朵在许多年前就已经失聪了。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