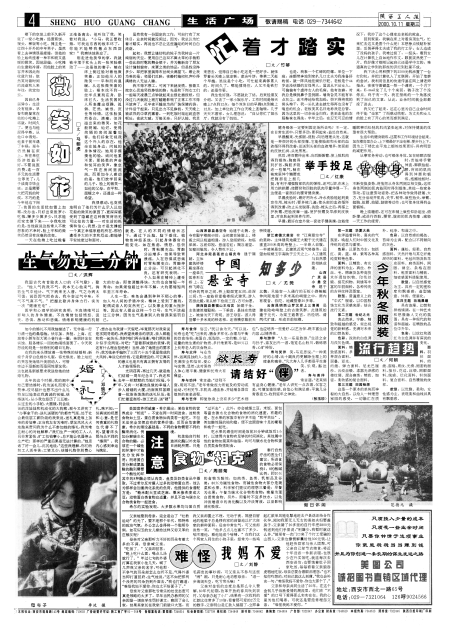
本版导读
难怪我妈不爱
文/刘静
父亲能娶到母亲,完全是沾了“社教运动”的光了。要不是那个年代,那特殊的政治气氛,外公怎么舍得将一个聪明伶俐、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这样又穷又笨的庄稼汉呢?
母亲对父亲那听力不好的耳朵有着太多的不满。母亲喊父亲:“吃饭了。”父亲却回答:“晚上吃什么面,喝点儿汤就行了。”年过七旬的外婆打算在我家小住几天,喊了几声我父亲的名字,可他那不争气的耳朵却怎么也听不见。气得外婆当即打道回府,生气地说:“还不如把那两个没用的耳朵扔到外面去。”我也打趣道:“难怪我妈不爱你,你也太不给面子了。”
母亲对父亲那吃亏常乐的处世态度可真是领略的太多了,早年当民办教师的父亲因留一调皮学生罚抄课文,晚回了会儿家,结果其家长在我家门前破口大骂,而我父亲却置之不理,无动于衷。隔壁自留地的畦梁子总是移我家的自留地以扩大自家的耕种面积,母亲非常生气,可父亲却淡然一笑:“他多占点儿也富不了多少,咱不理他,看他能成个啥精。”在我们这个两家人同住的小院子里,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闹,可父亲从不参与这些“闹”剧,只是耐心地劝慰母亲:“退一步海阔天空,吃亏常乐嘛!”
父亲对金钱的态度总是那么令人费解。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农村。父母亲办起了小厂,结果有一次收到的汇款比往常多了10倍,看着那可爱的2万元的数字,父亲明白是汇款人搞错了,立即拿起汇款单风驰电掣地赶去户县送还给合作伙伴。闻知我那无儿无女的表叔夫妇要盖房子,父亲骑了20多里的自行车把2800元钱送到他们手里说:“别嫌少,我暂时就这么多。”甚至有一次门口来了个打工受骗的山西人,父亲也慷慨解囊给他300元钱,让他赶快回家与亲人团聚。可父亲自己却节衣缩食,将近十年没添一件新衣服,也很少在外买饭吃。就连每次去西安进货,也要饿着肚子回家吃饭。每每看着父亲狼吞虎咽地吃饭,母亲总要含着眼泪埋怨:“也不知你咋想的,对自己就这么刻薄。”我也会补充一句:“难怪我妈不爱你,你也太那个了。”
父亲和母亲共同生活了20年。在这个金钱几乎战胜爱情的潮流里,他们在“不爱”的口号下爱得那么实实在在。我的心里为他们喝彩。可我还是要经常埋怨父亲:“难怪我妈不爱你。”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