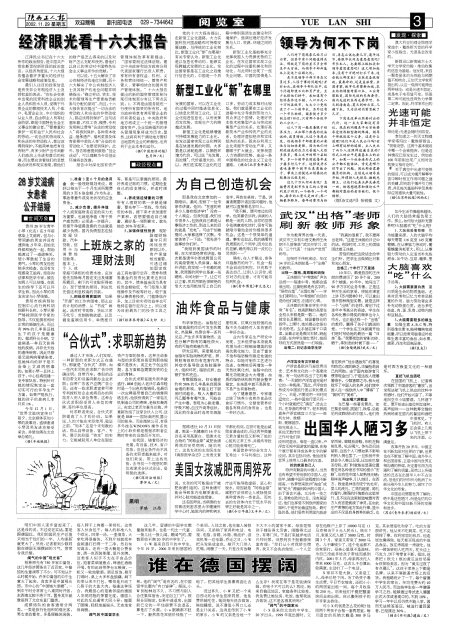
本版导读
谁在德国摆阔
咱们中国人逐步富起来了,这是没的说。不过说老实话,要是跟德国比,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他们的一半,人均差距就更大了。然而,记者看到少数同胞在德国无端摆阔的习气,常常令我汗颜。
阔气的中国“观光客”
柏林原先有750多家中餐馆,这几年经济萧条关了近百家,中餐馆的生意凋零了不少。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许多中餐馆的中午生意火了起来,食客多是中国观光团。市中心的“中国城大酒楼”,一到中午时分常常七八桌同时开张,东西南北腔不绝于耳,置身其中就像是到了北京东直门簋街。
成群结队的食客通常分两类。一类是旅行社组织的观光客,男女老幼都有,多是便鞋休闲装,每人脖子上挎着一架相机。这类客人伙食包干,每人的标准八九个欧元,四菜一汤,一壶清茶,大家吃得很痛快,不到片刻就把杯盘碗盏打扫得一干二净,然后匆匆离去。还有一类大概是公费食客,清一色西装革履,里外名牌。这类客人似乎不太在乎食品价位,抱着菜单随意点,啤酒红酒敞开喝,有的还自带茅台五粮液,一轮又一轮地敬酒。酒足饭饱、剔牙打嗝时,桌上大多杯盘狼藉,剩下的菜从来不打包,哪怕是只动了几筷子的大鱼大肉。每逢这种场合,我最担心的是被邻座的德国人发现同胞的挥霍无度。德国人对此的反应通常大同小异:瞪圆了眼睛,轻轻地摇摇头,无奈地耸耸肩膀。
阔气的中国留学生
这几年,留德的中国学生数量越来越多,也是一代比一代富、一拨儿比一拨儿阔。最阔气的,要数那些不满20岁的中学生了。
小W是来自四川的中学生,今年19岁,2000年来到德国柏林。他的“阔气”是有名的,在中国留学生圈内“有口皆碑”。据说,小W到柏林后不久,不习惯与别人合住集体宿舍,决定自立门户。按照合同规定,如果中途退房,出国前已交的一年住宿费不会退还,算是打了水漂。小w眼睛都不眨一下,毅然再花双倍价钱租了一个单间。入住之前,他先雇人装修房间,又添购了家具和电话、电视、电脑、音箱、冰箱、微波炉、游戏机等一应电器,乔迁之日,小W把头发染成金色,敞开大门供人吃喝,闹腾了一天,只差没有放鞭炮了,把其他学生羡慕得直吐舌头。
没过多久、小W又把一个来自西北的女学生招来同居,他免费供她吃住,她则每天洗衣做饭,陪他睡觉,说不清是小两口儿还是主仆关系。这消息传到了小W的家乡,小W的父亲是当地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干部,母亲觉得孩子铺张得太厉害,闹腾得太过分,有辱门风,于是打来越洋电话兴师问罪。没想到孩子挺着脖颈蛮有理:“你们从小对我娇生惯养,我又不会洗衣做饭,一个人怎么生存?我现在等于是花钱请保姆,有啥子不可以的么?再说,她来自偏远地区,家庭条件比较差,我免费让她住房、吃饭,她帮我洗衣做饭,这不是各得其所吗?”
“阔气”的中国家长
小X是来自北京的中学生,20岁出头。1999年底出国时,父母在他账户上存了10000马克(1马克相当于5元人民币)。转年7月,家里又托人捎了5000马克。时隔3个月,家里又带来了5000马克。儿子嫌钱少了,连个电话都不给家里打。母亲心里很不是滋味,为自己没能多给孩子带钱而感到内疚。2001年3月,母亲再次托人带来8000马克,这次儿子总算比较满意,主动打了一个电话。
X家并不是大款,父亲是工人,母亲已经下岗。为了给孩子凑生活费,平日节衣缩食,还把小小的两居室出租一间,每个月收房租250元。后来他们干脆把整套房间全部出租,自己搬到孩子的爷爷家去挤住。
可小X的钱是怎么花的呢?他同两个男孩子合租一套两居室,每月固定的花销大概是300多马克。其余便是吃和穿了。吃的方面很讲究,他从来不吃剩菜,吃不完倒掉了事。收到家里的钱后,他连饭也懒得做,每天都买现成的半成品食品,放在烤箱里一烤就吃,他的一顿饭够别人吃两天。枕头边上巧克力、饼干等零食不断。据说,他常把1欧元1根的黄瓜送给邻居女孩抹脸美容,因为“黄瓜过夜了有点蔫儿”。这孩子浑身上下都是名牌,从来不屑跳蚤市场上的旧货。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每个留德中学生的家长,年均花费大约10万人民币,而这些学生在一年德语学习之后,能够通过考试进入德国正式大学或者高中的,不到10%。学习一年半以后仍然不能入学,因而无法续签签证,被迫打道回国者,已经接近30%。
(摘自《书刊报》建政/文)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