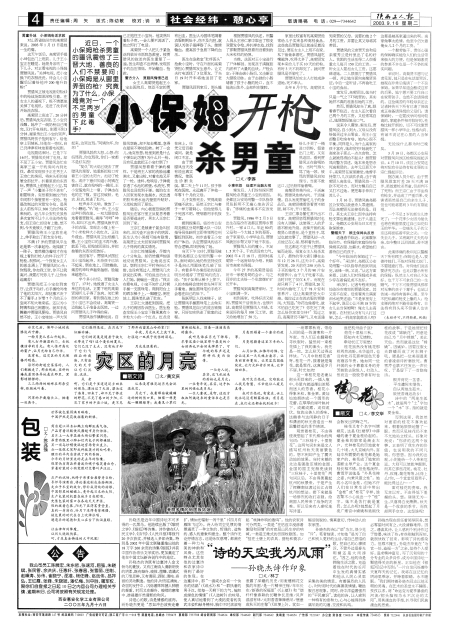“诗的天蓝我为风雨”
——孙晓杰诗作印象
□文/林丁
孙晓杰是近年中国诗坛不可多得的一匹黑马。他陆续出版了《黎明之钟》、《银狐》等诗集。诗作曾在《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日报》等报刊20多次获奖,并被选入多部诗集。特别是2002年中国文联隆重推出他的18万字260余页的诗集《银狐》并获中国作协伯乐文学奖后,更加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新诗创作中的地位。
孙晓杰的诗既有边塞诗人金戈铁马的豪放,又有江南诗人清新明快的阴柔,既有凝冷、峻拔、凿雕、诡谲式的刀笔思辨,又有清丽、洒脱、清纯、奇丽的灵动飘逸。他的诗,时而在清纯、奇丽的发抒中,闪烁着阵阵撼人肺腑的凝重,时而又在凝冷、峻峭的意绪中,渗浸着纤然清新的和风。
诗是心的歌。诗是情感的渲泻。而孙晓杰更是“思如冲击波疾走豪犷,情如光辐射一泻千里”(《四月有雁阵飞过》)。诗人给司空见惯的情景通灵了一种立体的、哲理的、造势的、感人的意象和意念。整个诗作无论抒情言志,还是咏叹感喟,都满充着一种力与美的神韵和风骨。这些特点尤其在他的边塞诗和农家诗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在边塞诗中,那“一滴咸水会有一个快乐的结晶”(《咸水》)和“一群执著的男子汉,把每一天剩下的力气,编织成绿色的情愫”(《人造树》)的咏唱,使人真切地看到了大漠拓荒者的英武丰姿和献身精神,胸中不时滚滚响起“核弹炸响的轰鸣”。他的农家诗可分两类,一类是“在枯涩中浸渗着激励和同情”的对底层山民生存的呐喊,一类是王维式的田园牧歌图。如“挂在土壁上的农具、猎枪和蓑衣/泄露了深藏的历史/用麦穗棉花交换的年画/是一片精神庄稼/年年长在/新春的祝福里”(《土壁》)和“烟杆杆像春耕的长鞭伸长思绪/风声滋滋有味/太阳香香辣辣燃尽/惬意成秋天的庄稼”(《田埂上》)。犹如一幅活脱脱的、情真意切,传神动人的农家图。
孙晓杰的诗以“颂”为主,很少见“斥”。笔者细读,才知他“是为了自己和别人更好的生活,唱自己想唱的歌,把自己的心事倾诉,不管外边是春光明媚还是大雨滂沱。”因之,他的诗是拥抱生活之歌,充溢着他在时代的长河中生发的真情实感和他从人民心灵里采集的美的情思,有着强烈的人民心,时时用时代的真善美情愫,鞭挞假丑恶现象。同时,诗中洋溢着强烈的“平民意识”,读他的诗,让人感到一种特有的亲和力,心与心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勾通、交流和共鸣。
孙晓杰现在担任着领导职务,想必零星时间有之,大段清静难得。因之,通读其诗,让人感到个别诗作过于惜墨,味淡了些;有些刚触到深刻,就很快收了回来,影响了诗的感染力。但瑕不掩玉,孙晓杰毕竟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之余,坚持个人爱好,追求精神富足,写了沉甸甸的十分专业的众多诗作,成为中国诗坛一颗值得关注的新星。正如他在《银狐》后记中写到:“一片白发闪烁着昨天复昨天的记忆。我将在这记忆的阴凉里乘凉,并睁着眼睛,永不睡眠。”我们期待着孙晓杰同志以他无瑕的灵魂,在艺术的圣堂永不睡眠、孜孜以求,将“命运变为夏季暴涨的河流/把头脑视为永不沉沦的太阳”,用其滴血的手指,扒寻我们民族滴血的思索。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