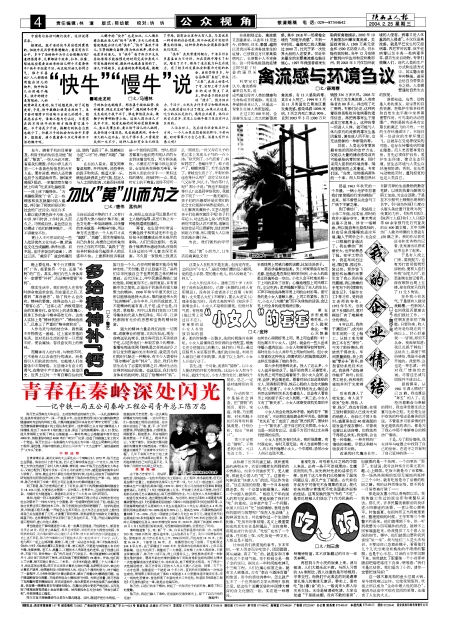
我的企业情结
□文/周宁光
那是1963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一辆小毛驴车拉着我们家简陋的行李向棉纺厂走来,却不曾想从此会与工厂结下不解之缘。
到了棉纺厂,我插班上小学二年级。说实话,那时的我并不是好学生,算术考试总是不及格,拼音一塌糊涂。所以挺自卑也挺孤独的,好在后来我慢慢地适应环境,融入于同学之中,也会说一口顺溜的普通话了。我在棉纺厂渐渐长大,也开始熟悉了她。在学工劳动中,我在车间扫过地、摆过管、推过纱、装过纬。那纱锭飞旋经纬如瀑的场景引发了我心灵的强烈震撼,我以稚嫩的手笔写下的《摆管机诞生记》、《摇纱女工》等习作,受到语文老师的夸奖。1972年冬天,当我欲下乡插队时,竟对棉纺厂有了难解难分的情结。
9年以后,我终于调回该厂,成为织布车间的一名上轴工。从技工变为辅助工本有些“掉价”,可为了那份情结,我依然干得欢实。车间质量抽检,我上的轴“零分车”最多;参加省纺系统技术比武,我获得“省级操作能手”称号;担任男工班长,我和我的班组并列于光荣榜上。
后来我调入了收发室。有人说干收发“位卑、岗低、人背、钱少”,我也有同感。在领工资时看到别人已成为光荣的纳税人,而自己才领5张时;盛夏里在近40度高温的收发室汗浸衣襟时,尽管我也曾以此话自嘲,但我依然干得那么欢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奉献,一种对棉纺厂情结的奉献。尽管这奉献与收获并不对称。
改革的时代鹰击长空,日新月异的生活激励我勤奋笔耕,以我的执着与激情为职工加油,为企业讴歌。于是在不少报刊上频频出现我的名字。《中国纺织报》几度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我为我厂传真的力作,《陕西日报》、《陕西工人报》和《工人日报》等60余家报刊先后刊登我的近400篇文稿,其中为棉纺厂人歌功颂德的文章就有150篇之多。我的作品获奖证书和优秀特约记者、优秀通讯员获奖证书也多了起来。
于是有人找上门来,要我捉刀,也有为打官司找我写诉状的,更有人在打听我“润笔几何”,甚至连贼也惦记着我,深夜顺阳台爬上五楼,却在我家只找到了11元5角钱。
在外我小有名气,于是便有人鼓动我跳槽,一些新闻人也问我是否愿意去他们报社工作。一位朋友甚至拍了胸膛:只要你来,收入绝对是你现在的三倍以上。好心好意我一一皆领,却恕不从命。我深深知道:我已扎根于棉纺厂这块沃土,深浸于那份情结,我是不会离开她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忠诚,一种对我厂情结的忠诚。尽管这忠诚与回报并不成正比。
屈指算来,从1981年调入棉纺厂已21载,我也算是“奔五”的人了。在经历着勤奋与奉献的同时,我也承受着生活之重与生命之轻。无论是生活中欢快的吟唱还是痛苦的诉说,不管是岁月里深情的抒发还是肤浅的表白,都是为了我心中那个难解难分的棉纺厂情结。
于是,为了那份情结,我在浮华与喧嚣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在追寻之后看到了自己延伸的路……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