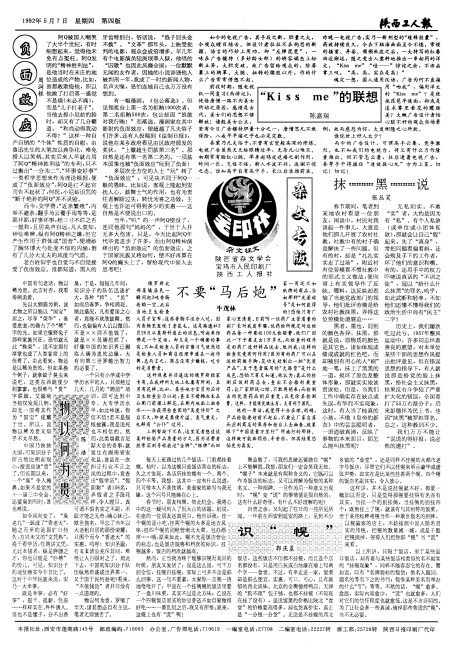负面效应
周润根
阿Q被国人嘲笑了大半个世纪,有时细想起来,觉得他未免有点冤枉。阿Q发明的“精神胜利法”,是他当时在未庄的地位造成的产物。比如,谁都敢欺侮他,所以他挨了打后第一感觉不是痛(未必不痛),而是“儿子打老子”。当他去捏小尼姑的脸时,却又有了几分霸道:“和尚动得我动不得?”这样一种自产自销的“个体”性质的自慰,由鲁迅先生的大笔加以典型化,难免授人以笑柄。其实后来人早就占用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专利,只不过搬出“一分为二”、“坏事变好事”一类哲学思想来作为理论根据,便成了“负面效应”,阿Q是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了,何况,小尼姑诅咒的“断子绝孙的阿Q”并不灵验。
而今,交学费,“近亲繁殖”,内举不避亲,翻手为云覆手雨等等,是耶非耶,好事坏事,经三寸不烂之舌一搅和,且居高声自远,凡人莫知,神仙难辨。纵有阿Q精神之嫌,但它产生作用于群体或“国营”,便增添了胸怀博大与处变不惊的内涵,倒有了几分大丈夫的风度与气质。
老百姓似乎也自觉与不自觉接受了负面效应。谁都知道,黑人的牙齿特别白,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文革”那年头,上映受批判的电影,观众会成倍增多。早几年有个电影演员犯流氓罪入狱,他唱的“囚歌”也因此风靡全国;一位默默无闻的女作者,因她的小说诽谤他人被判刑一年,竟成了一时的新闻人物,名声大噪,恐怕连她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
有一幅漫画:《包公落选》。但见领奖台上第一名为拒贿1000次者,第二名拒贿500次,包公却因“谁敢对我行贿!”而落选。漫画家在其中影射的负面效应,便超越了凡夫俗子们许多。还有人投稿到《法制日报》,说他在某乡政府看见由区政府颁发的奖状:“上缴超生罚款第三名”。那自然是还有第一名第二名的。一项基本国策也被“负面效应”玩到了负面!
多层次全方位的人士“玩”转了“负面效应”,可见决不同于阿Q一般的愚昧。比如说,客观上能起到安抚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也有为责任者解除过失,转忧为喜之功效,主观上也许还可得到多少的实惠——这自然是不便说出口的。
当年,“叭”的一声阿Q便没了,连同他那句“妈妈的”,于世于人并无多大伤害。只是,今天比起阿Q年代毕竟进步了许多,而由阿Q精神演绎出的“负面效应”的负面效应,之于国家民族又将如何,便不好再算在阿Q的癞头上了,留给现代中国人去思考吧!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