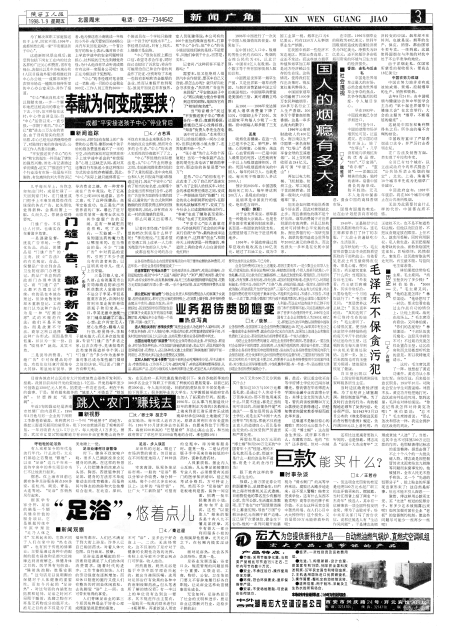
奉献为何变成要挟?
——成都“平安接送孩子中心”停业背后
文/占若观
为了解决双职工家庭接送孩子上学、回家不便,1996年,成都悄然出现一家“平安接送孩子中心”。
这道新鲜风景出现后,就受到包括下岗女工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心和赞赏。省市电视台、各报社以及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海外版》都相继赶到中心办公地——成都市双桥子农贸市场边一幢陈旧招待所里的中心办公室采访,并作了报道
“中心”乘此良机本可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把这桩高尚的事业干下去、干好,但不料恰在这时,中心传出消息说,自“中心”运营以来,一直亏损,一学期下来后,“中心”已“栽”进去三万左右的资金。由于没有坚实的经济后盾,中心已经无法再继续经营了。对陆续打来的咨询电话,公司工作人员表示抱歉。
“平安接送孩子中心”的夭折”和它的诞生一样引起了媒体的强烈兴趣。首先,有记者通过采访调查,证实了“接送孩子”这个行业没有市场一说是站不住脚的。有位离休的刘大爷告诉记者,他为接送在小南街读一年级的小外孙,每天要坐四站58路公共汽车来回往返6次。一个省公安厅的张女士表示,她对孩子在上学放学途中的安全问题特别担心。社科院的王先生则颇觉奇怪:为什么他没有早点听说成都市有这样一家服务公司呢?他正在为接送孩子犯愁呢。
“中心”的李经理对笔者算过一笔帐:他一月的办公室租金900元,工作人员工资约3000—4000元,同时还有在报上的广告费和办公费用,靠那30来个孩子给的服务费显然填不了一半的亏空。而有的家长对这突然在孩子上放学途中杀出的“有偿服务”心理上还缺乏认同,或对其还靠自行车驮送小孩这种陈旧方式的安全性存有疑虑。因此,“中心”实际上就只能停滞在一个接送员在一个学校只能接送一个孩子的“初级水平”上。李经理总结说,只有上档次,上规模才是出路。
“中心”很快在报上露出口信,希望寻求合作者。同时自己也拟印了诉求信,将合作可能带给自己和合作者的利益作了论证,分别寄给了本地一些较有影响和资金雄厚的企业。然而从寒假开始到现在,虽说开初反应非常强烈,不仅有本地企业来联系合作,外地的反应也积极。然而对众多的合作者,“中心”均未进入实质性的协商就不了了之。
“中心”李经理的实际想法是:从“中心”开业到停业之间,本地新闻媒体都对他们作了大量的报道,连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海外版》都报道过他们,因此“平安中心”已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如果哪个企业能出资和他们合作,必将在广告宣传方面获得丰厚的回报,以通常的广告方式和同样数额的投资要获得这样的回报是困难的。因此,没有理由为此一时的困境感到悲观。
那么问题又出在哪儿呢?
记者问李经理:“你所希望的档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李经理说:“主要希望在交通工具上改单一人力车为微型汽车加部分人力车。”
成都出租车公司的办公室人员张建伟说:本公司有约200个座位的微面出租车,打算和“中心”合作,但“中心”的张小姐却说他们缺的是钱,不是要车。问他们拿钱干什么,回答是:买车。
记者问:“这种回答不是矛盾吗?”
需要车,但又拒绝别人提供汽车合作经营。要买车自己又没钱,那怎么办呢?就只好向社会寻求资金,“然后用广告宣传来回报”。“平安接送孩子中心”所以有能力使合作者得到这样的回报,是因为它有了“相当的知名度”。
当“知音婚介”找过“平安接送孩子中心”联系合作一事后,竟感到委屈,感慨自己好心没得好报。“知音”负责人李先生在电话中对记者说:“本来我们说可以给他们提供一间办公室的,但那边的张小姐太傲了,连答复都不给一个。”“张小姐”为什么不给个答复呢?当另一个做农副产品生意的胡先生去电话了解资助事宜时,那边给的答复是要“60万”!
显然,“中心”的初衷也于此改变了,为了自己的“迅速发展”,为了让别人给钱买车,对社会的承诺和责任倏忽之间,变成了一声轻描淡写的“抱歉”!社会的关心和新闻界的宣传,在膨胀的私欲触媒作用下,变成了当今社会上已成套路的商业炒作。“奉献”变成了赚取甚至索取,“停业”也成了无奈的要挟。
“平安中心”拉大旗做虎皮,巧妙地利用了社会给的声誉来行自我“炒”作,最终欲成幸运的暴发户。这样来“创业”,和期待天上掉肉饼是一样荒唐的。难道世上真的会有人白白送钱给他们吗?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