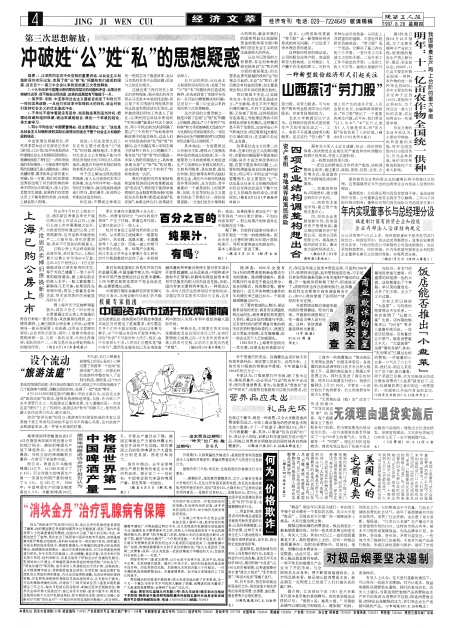
本版导读
第三次思想解放:
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
提要:1、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克服了姓“公”姓“私”问题给我们造成的困惑,这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2、十九年改革中显露出来的那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如果没有突破性进展,就可能会出现倒退,改革的成果就有可能毁于一旦。
3、俄罗斯、东欧、中亚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目前走了和我们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一旦他们在改革中取得较大的转机,就会对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造成冲击。
4、不争论不意味着就没有是非,当实践发展到适当时机,把理论权威和组织权威、政治权威相结合,做出一个权威的结论,供大家学习。
5、邓小平同志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也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得出的适合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
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研究员李君如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江总书在中央党校讲话时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准确地反映了我们这一、两年来面临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进入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时期,要求改革必须有重大突破;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理论界却出现了对目前形势的种种不同的认识和观点,使人们的思想发生困惑。如果我们在思想认识上不能有新的突破,在实践上就会陷入困境。
他说,人们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的主要分歧是姓“公”姓“私”的问题,概括地讲,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能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不同认识,具体地说,就是对目前所有制的结构和实现形式的不同认识。
对于怎么解决出现的困惑和疑惑,有人从马克思的本本中找答案。在去年和今年初一些流传的打印稿中,就出现成段成段地引用马、恩的著作,来说明公有制应该是怎样的。
相应地,不赞成这种观点的一些同志为了推进改革,也从马克思的本本中去找证据,论证与之相反的观点。
这就出现了我们历史上常见的奇特现象,观点相左的双方都从马克思本本里面找证据,而且接下来又围绕马列经典作家的这段话和那段话发生争论。这样就使我们研究工作进入了误区,江泽民同志讲话中所说的“学风问题”就是针对这个误区的。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明确了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来判断改革中的是非得失。过去人们对市场经济的姓“社”姓“资”有疑问,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和十四大上已经解决了。现在姓“社”姓“资”的问题进一步深入到所有制层次上,具体地表现为姓“公”姓“私”的问题,这也同样要按“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统一认识。
我们不能把对所有制结构和国有经济的任何变革都说成是“私有化”,特别是不能简单地把现代企业制度和股份制(包括股份合作制等)都看成是搞“私有制”,如果这样认识,改革就无法深入。
总书记的讲话,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克服了姓“公”姓“私”问题给我们造成的障碍,系统地回答了实践中存在的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这次讲话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冲破了在姓“公”姓“私”问题上的疑惑,提出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具体地说,一方面要保证公有制为主体,继续大力发展各种非国有制成分的经济;另一方面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大胆利用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各种形式搞好国有企业。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是非常深刻的、全方位的,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国际上的俄罗斯、东欧、中亚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目前走了和我们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一旦他们成长中取得较大的转机,就会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比如国际资金的吸纳等方面)和我们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造成很大的冲击。
从总书记讲话的大背景看,存在的种种困惑包括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错误观念,但主要是由那些超越阶段的“左”的观念引起的。无论“左”和右,背后都会有利益的因素,但主要是观念和认识本身的因素引起的。
我们提倡不争论,让实践来发言,争论的结果是造成对立,产生极端,而且不利于理论问题的解决,不利于实践的发展,又伤害了团结。这种局面的存在客观上导致理论界的不同派别此消彼长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不利于发展的。应该学会心平气和地讨论,相互吸取对方意见中正确的部分,在实践中去证明、去发展。
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第二次革命。在面对社会主义改革问题时,首要的问题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其次才是怎样改革的问题。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上,主要的阻碍就是来自旧体制的旧观念,所以邓小平同志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这也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得出的适合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非常深刻。(摘自8月12日《中国经济时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